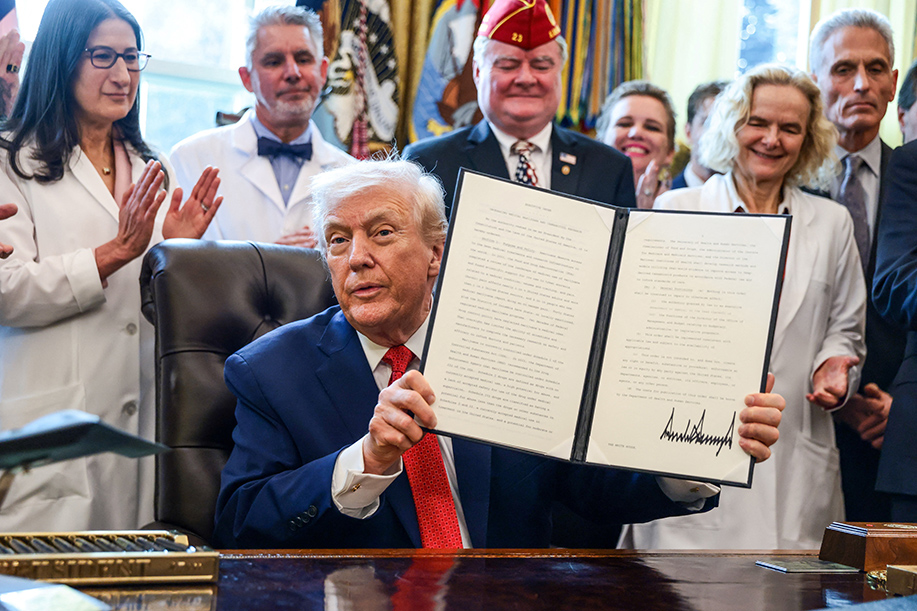陰雲密佈的清晨,努倫·納比將竹竿和鐵皮裝上木船。他一年前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上脆弱小島上建造的家園,正面臨被洪水吞沒的危機。
這位養育四個孩子的農民一年內已第二次被迫遷徙。
“河水每天都在逼近,”納比聲音因疲憊而緊繃,“我們生來就該受苦。這場抗爭永無止境。河水沖走我家多少次,我都數不清了。”
50歲的納比別無選擇,只能遷往另一處沙洲——由河流沉積物形成的臨時島嶼。他的稻田和扁豆田早已被布拉馬普特拉河吞噬——這條發源於喜馬拉雅山脈的河流,流經中國和印度後最終抵達孟加拉。
“新家園會怎樣?”他望著寬闊的褐色河面說,“運氣好能撐幾年,差勁的話一個月就完了。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一夜消失的土地
每年,孟加拉北部庫裏格拉姆縣數百戶家庭都面臨相同命運。河岸崩塌時,人們不僅失去家園,更連同土地、莊稼和牲畜盡數喪失。曾為數百萬民眾提供生機的布拉馬普特拉河、提斯塔河與達拉河,如今變得難以預測,侵蝕土地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
散佈於北部平原的沙洲島嶼——這些沙質漂移島嶼——是孟加拉最脆弱的區域。居民們反復重建家園,卻總被河水奪走一切。
“洪水毫無徵兆地襲來,”70歲的農民哈比布·拉赫曼說,他曾在多個沙洲島上生活過。”夜晚入睡時,黎明時分河岸已悄然移動。醒來時已無家可歸。我們的生活沒有片刻安寧。”
當全球目光聚焦於11月10日至21日聯合國氣候峰會東道主巴西之際,孟加拉的抗爭為各國領導人敲響警鐘。這個國家常被譽為韌性典範——修築堤壩、完善洪水預報、開創社區適應模式。但若缺乏更強有力的國際支持與氣候資金,這些努力終將功虧一簣。
“當地民眾正為非己所致的排放付出代價,”水資源與氣候變化專家艾努·尼沙特指出,“若COP30峰會具有實質意義,就必須為損失與損害提供切實資金,幫助像我們這樣的脆弱國家在為時已晚前守護生命與土地。”
氣候變化的直觀呈現
科學家指出,庫裏格拉姆的現狀正是氣候變化的直觀呈現——源自布拉馬普特拉河與提斯塔河的喜馬拉雅冰川正加速消融。
“冰川融化速度已達1990年代的近兩倍,”氣候專家尼沙特解釋道,“過量融水湧入下游,使本已暴漲的河流雪上加霜。”
與此同時,季風變得愈發異常——來得更早、持續更久,且常以強烈的驟雨形式降臨。“季節節奏已然改變,”尼沙特指出,“降雨時量過大,停雨後又常出現乾旱。這種不穩定性使水土流失和洪災問題急劇惡化。”
他補充道,孟加拉碳排放量不足全球總量的0.5%,卻承受著氣候變化最嚴重的後果。
世界銀行預測,到2050年每七名孟加拉人中就可能有一人因氣候災害流離失所。
對50歲的科西姆·烏丁而言,遷徙已成為常態。這位七個孩子的父親說:“在我有生之年,河水已吞噬我家30至35次——或許更多。”
“每次重建家園,河水又會捲土重來,”烏丁凝視著河面說,“但我們還能去哪里?如今整個世界都成了汪洋。”
女性承受著頻繁遷徙的沉重負擔。30歲的莎希娜·貝古姆育有兩子,她回憶去年洪水期間腰深涉水為家人做飯的情景:“十年間我們搬了六次家,每次剛重建家園,河水又將一切卷走。”
對莎希娜而言,每次遷徙都帶來新的艱辛。“對婦女和少女來說更難,”她解釋道,“我們既要尋找乾燥的土地,又要做飯照顧孩子——更沒有隱私和安全可言。”
為生存而建
在凱亞爾阿爾加查爾地區,當地組織安裝了土工袋——這些裝滿沙子的巨型麻袋能加固河岸抵禦侵蝕——約300戶家庭得以在此安居三年。
“土工袋帶來了巨大改變,”39歲的喬胡魯爾·伊斯蘭說。在此定居前,他已十多次失去家園。“過去三年河水再沒吞噬我們的土地。我第一次對未來有了些許信心。”
當地非政府組織還協助建造了高架村落——將房屋群架設在地面之上,以抵禦季節性洪水。
站在堅守三年的河堤旁,伊斯蘭流露出謹慎的樂觀。
“或許河水終將再度來襲,”他微笑道。周圍孩童在堅實地面嬉戲,歡聲笑語隨晚風飄蕩。“但這次我們已做好準備。此刻土地仍在支撐——我們亦然。”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