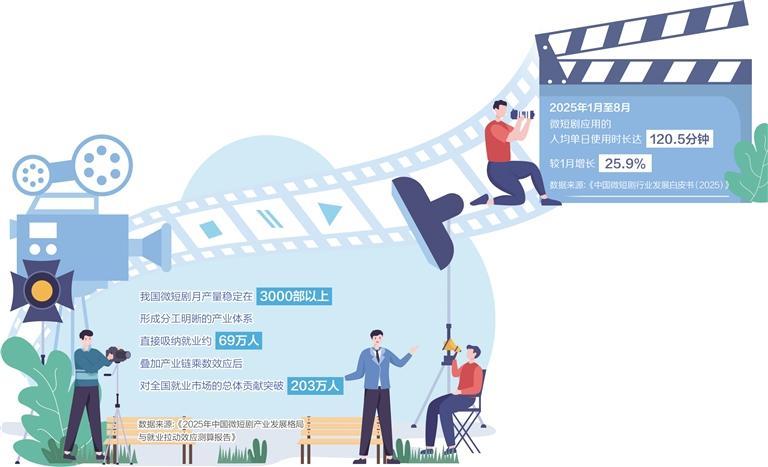隨著特朗普政府的上臺,其在如何對待中國的關鍵方面仍是未知數,尤其不確定的是,特朗普團隊將就“中國威脅”的性質和範圍達成何種共識。國務卿魯比奧在確認聽證會上稱,中國是“我國迄今面對的最強大、最危險且幾乎勢均力敵的對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華爾滋稱,“我們正與中國冷戰”,因為中國的目標是“用中國夢和中國的領導取代美國夢和美國在全球的領導”。
特朗普本人是否認同這種對中國威脅的看法?他很少(如果有的話)用類似的戰略或意識形態話語談論“中國威脅”。他的做法通常被描述為更多的“交易性的”。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顧問們還應重新審視魯比奧和華爾滋對北京戰略意圖的看法。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梅拉妮·西森的新書《美國、中國,以及控制權的競爭》將使他們受益匪淺。西森令人信服地駁斥了有關中國試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觀點。
中國外長王毅與魯比奧首次通話時表示,“我們無意超越或取代誰”。那些聲稱中國謀求稱霸世界的人似乎從未正視過這一論點的邏輯。
他們非常熟悉歷史上其他大國多次爭奪地區或全球霸權失敗或無法維繫的原因。正因如此,北京才會把重點放在最大限度地擴大中國在多極世界中的財富、實力和影響力方面。中國領導人幾乎可以肯定地認為,這是比與美國展開“贏家通吃”競賽更可行、更務實的方法。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日益增長的相對實力、“全球南方”國家的接受度,以及美國實力和影響力正在受到的限制,北京可以從中獲得優勢和機遇。
這就是西森在書裏講到的“控制權競爭”。這不是一場零和競爭,因為中國的目標不是奪取美國的角色,單方面制定國際行為規則,而是在制定規則方面增加其相對美國的作用。這裏的核心觀點之一是,中美兩國的利益相互競爭,但並非不可調和。正如西森觀察到的,認為中國想構建“本質上與美國對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沒有證據的判斷”。
如西森所言,華盛頓真正面對的是“中國成功證明了其政治體制在社會上是穩定的,在經濟上是富有成效的,在軍事上是有能力的”,而這本身“會使美國更難追求其目標和利益”。這加劇了“一種焦慮,以為一個讓北京更大地行使國際領導權的世界,將是一個敵視自由主義原則並對美國構成威脅的世界”。這又助長另一種誇大的觀念,認為中國試圖以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破壞世界秩序。
這種誇大的威脅感有幾個目的。將中國視為生存威脅,使華盛頓可以轉移對自身弱點的關注,這些弱點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力。它還轉移了與北京進行建設性接觸所需的艱難政策選擇。最後,正如西森憂心忡忡表示的那樣,有關中國謀求全球霸權的論調,正被用作對抗北京和排他性競爭的理由,而這很可能會增加美國的代價和風險。
為了支持另一種觀點,即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西森簡要回顧了華盛頓和北京各自對待1945年後國際秩序的歷史。總的來說,西森認為,中國“不但沒有選擇退出,也沒有試圖阻撓或推翻戰後秩序的體制”,而是“融入了這些體制,並在其中的程式中努力獲取和施加影響”。儘管北京公開批評某些規則,但其一直從體制內宣導改革,並在這一過程中“加強自己的談判地位”。“從過去和現在中國的言行來看,中國更多的是支持而非反對”戰後秩序的基本原則和制度。
西森表示,儘管歷史非常清楚,但華盛頓的許多人對美中競爭採取了一種說法,一方面堅持美國對戰後秩序的依戀,另一方面認定中國打算用其他秩序來取代戰後秩序。這種說法掩蓋了生存威脅與地緣戰略挑戰之間的區別。
那麼該怎麼做呢?西森最令人信服的觀點之一是,美國的說法“使秩序成為大國衝突的目標,而不是管理大國衝突的手段。這是一種危險的顛倒,它把國際事務規則的談判變成了制定規則的競爭”。華盛頓需要認識到,它不能單方面決定美中關係或國際秩序的條款。
相反,美國只需通過與北京的持續戰略接觸,著手確立那些條款。西森表示,雙方有共同的工作基礎,並非不可調和。儘管雙方都在尋求最大限度地擴大自身的財富、實力和影響力,但也都稱“持續支持”許多共同的原則和目標,包括“希望維持一個以促進全球貨物、資金、思想和人員流動的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
與西森的觀點類似,中國的美國問題學者王緝思最近強調,北京和華盛頓需要克服戰略不信任,在關鍵的全球和雙邊問題上達成“戰略共識”。他觀察到,美國懷疑中國的目標是推翻現有的世界秩序,而北京則懷疑華盛頓的目標是推翻中國的政治制度。雙方都不相信對方做出的否認。王緝思說:“只有雙方放棄零和競爭思維,中美關係才會有更光明的未來。”
來源:環球時報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