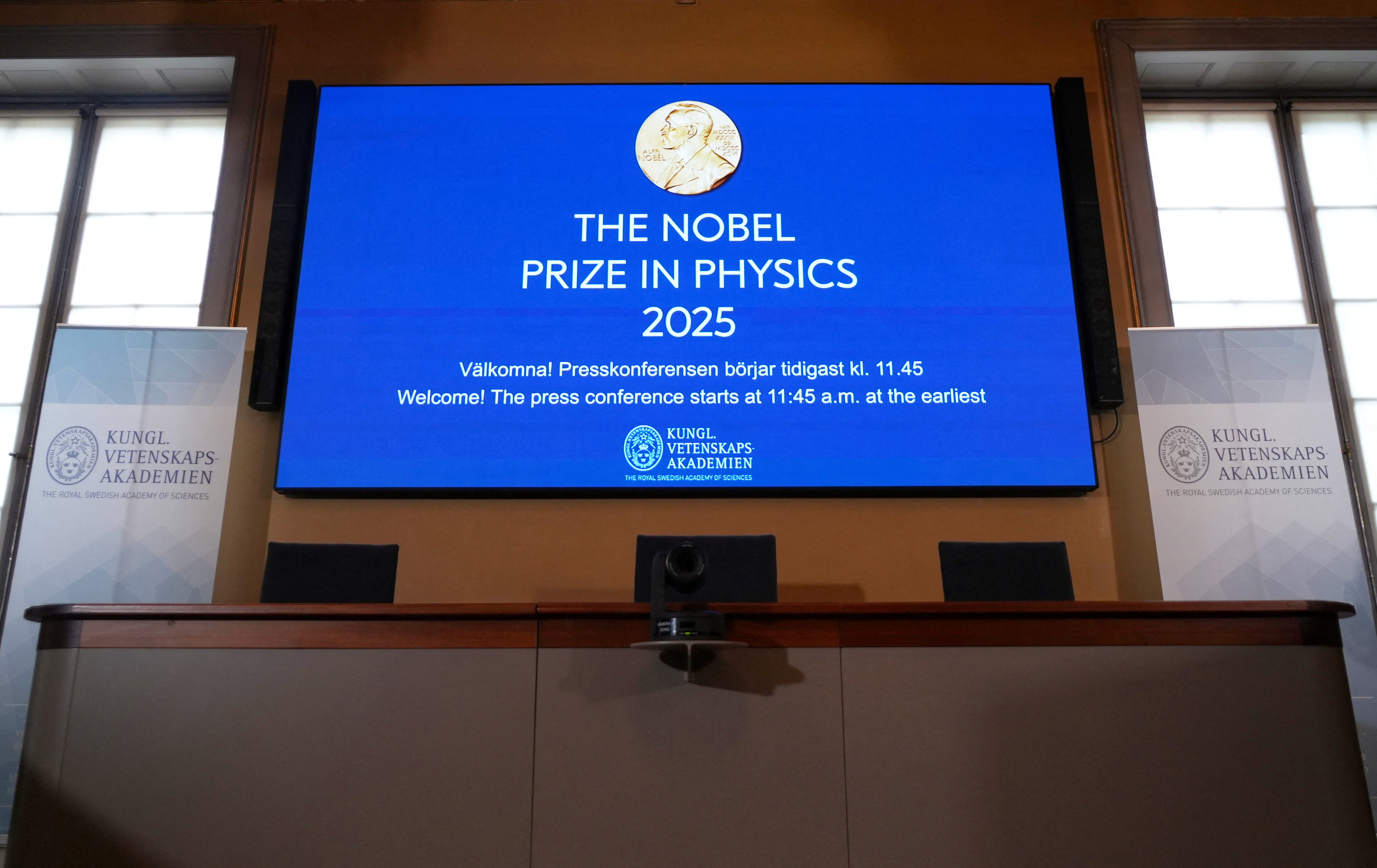羅懷臻教授形容自己的戲曲創作過程好比釀酒,“花費的生存時間和生命能量構成它的精神含量”,我也在對本書的反復閱讀和體悟中,逐漸探索出一個用來解讀羅教授文藝思想的重要概念:距離意識。

《羅懷臻演講集續編·2023》 羅懷臻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距離意識
距離意識也許源於劇作家觀察生活、審視現象並挖掘本質的職業本能,更有賴於羅教授在地緣屬性和文化屬性上秉持“資深的新上海人”的旁觀式自我定位。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20世紀80年代啟蒙思想對他的思維和意識的根源性影響。距離意識更體現在他對於“傳統”和“現代”的辯證性理解。在他的認識中,作品的品質可以超越時代和族群的隔閡。屬於過去和未來的作品,因其思想內涵中有能夠與當下觀眾的接通之處,而讓古人與今人的心靈距離無限拉近。
在作品創作方面,羅教授的距離意識首先體現在他對素材的處理手法和介入角度上。他在本書中回答了文藝理論中永恆的關於“真、善、美”的關係問題,總結出“真的挖掘、善的過濾、美的境界”的創作“公式”。也就是說,要盡可能地感悟出源於人類生活和普遍人性中的“真”,但這些形象和事件,要經過“藝術化的再現”,能夠在良心、正義、公理等道德層面令觀眾接納和認同,再經過諸多藝術部位的設計和錘煉,才能成就形式和內容的美感。可以看到,羅教授對筆下角色的人格都會進行遴選和提純,主要人物經過唯美化、加魅化,總有一層高貴的底色。即便是反派角色,也壞得坦然俐落,鮮有猥瑣和賤相。作品對於生活現實,是彼此互映、若即若離的漸近線,體現出羅教授對瑣碎、中庸、低俗始終保持距離的創作偏好。
現代性
羅教授的發展觀念要求作品有長久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從歷史本質中來,從人性普遍中來,從情感共鳴中來,歸根結底,還是要依靠作品的現代性。羅教授指出:“‘現代性’是一種品質,是由人文價值觀、表演形式和演藝空間共同構成的。”他還從多個層面論述了現代性這一他最為看重的精神屬性。首先是現代性的界定——現代不意味著與傳統的割裂。“傳統實際上是流,不是源。源是生活,生活是人性。藝術、文化都是生活提煉出來的。”每一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經典作品,都由對時代感悟最強的創作者,在一定的文化風氣和表達方式下締造。當代語境下,那些最“出圈”的文藝作品莫不如是。藝術家都經歷著在承認經典的前提下,追隨經典、打破經典、再造經典、成為經典的迴圈過程。羅教授還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強調,藝術家雖然無法超越時代,但可以克服時代的局限,完成表達時代、回應時代的使命,這就具備了現代性。
其次是對現代性的品質要求——作品中的強烈情感共鳴,需要更具普遍價值的理性意義。羅教授批判了舞臺藝術作品中盲目煽情、空洞說教、否定人性、有違當代人價值觀和共識的情節。因為“現代性是符合人類永恆價值、基本價值,超越現實、超越時代的審美觀照”。現代性還肩負著更新時代表達的使命。具有現代性的作品,體現出時代的處境和學問。羅教授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屬於它的特定情感呈現,體現在創作上,也就要求劇作家能在不同時代找到適合自己的創作契機。”
人之本
關注人,表達人,反思人,不但是羅教授多年來奉行的創作原則,也是他理解和評析藝術作品的核心準則。他認為,題材不分古今,“共同著力的都是表現人在特殊歷史環境中的生存境遇和人性的表達。”人本觀念不是臺詞裏的口號,不是論述中的標語,而是貫穿在形象的誕生、特性的顯現、主題的深化等具體層面,並因距離意識而有了獨特性。
羅教授少年時代的閱讀經歷中,尤其以《說嶽全傳》《雷雨》《九三年》三本書型構了他受益終生的文學理念,那些在危機四伏中百煉成金、追求真理真義的偉大人性,為他種下了人本意識的種子。
民間生活和原鄉情懷,滋養著羅教授的人文根基。對理想的追尋,對命運的感慨,對痛感的咀嚼,逐漸造就了他獨一無二的生命經驗和藝術表達,確立了他具有民間感、崇高感、抗爭感的作品主體性,“一個作家的生命一定是不能乾燥的、不能單調的,一定是貼著人物的心去寫作的。”因此,比起生活苦難,羅教授筆下的人物更多的是在經歷心靈苦難。
羅教授將他的主人公作為一個大寫的人來塑造,肯定他們的價值和尊嚴,表現他們的複雜性和本質性,尋找他們在命運的洪流中頑強抵抗的內在動力。羅教授在創造人物時的出發點依然與距離意識有關。以他對《白蛇傳》的改編(即新編越劇《蛇戀》)為例,白蛇修成人形,卻在融入人類社會的過程中,越來越深刻地對人類社會的種種“潛規則”提出質疑。白蛇用自然之道的眼光,迷惑不解地打量著人類社會的“約定俗成”“向來如此”,這就形成了對人的群體性反思。舞劇《朱鹮》《大河之源》《AI媽媽》的矛盾衝突,亦是以不同物種之間的隔閡與理解來展開設置的。“由異類的眼睛來看人生,這樣比由人類看人類可能看得更清楚,更深刻。”另外,羅教授從角色性別的角度總結道:“女性通常是我塑造的理想人物,男性則通常是我塑造的現實人物。”看似男女不相容的設置,並沒有走向性別對立的議題,而是希望引發更深的關於人性和真善美的思考。或許在羅教授的心中,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竟不比性別間的差異更少。
正因為羅教授遵循了人性本身的複雜和糾結,遵循表達的率真、向善及審美,往往能贏得絕大部分觀眾對人物的認同。尤其是將人物置於多種情感關係的矛盾中,去試煉人存在的價值。人物的情感取向基本等於他的人生取向,這是羅教授的作品與觀眾共振的一個基本點。
在堅持人本觀念之上,羅教授也在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完成著自我更新。在他的前期作品中,總有著一種揮之不去的蒼茫感,金龍(淮劇《金龍與蜉蝣》)、西施(越劇《西施歸越》)、班昭(昆劇《班昭》)、“妻”(甬劇《典妻》)等代表性人物,內心都在比較、在糾結,忍不住要質詢事物的意義,質詢秩序的合理性。而本書中的相關作品及論述,則體現出對崇高價值的篤定感:“雖千萬人吾往矣。”
羅教授帶有距離意識的人本觀念,還體現在近年他從文明意識和生物性的層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展開的反思。在疫情期間,他“思考苦難,思考生命共同體、人和動物甚至人和微生物之間的關係”。在舞劇《大河之源》中,羅教授確立了“人類與山水,人類與生靈是一個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這一思想主題。舞劇《AI媽媽》“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哲學源頭,對人的定性進行追問”。這些藝術探索和理論總結,都體現出羅教授從破解人類心靈密碼到破解人類文明密碼的不斷嘗試。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講師,博士)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