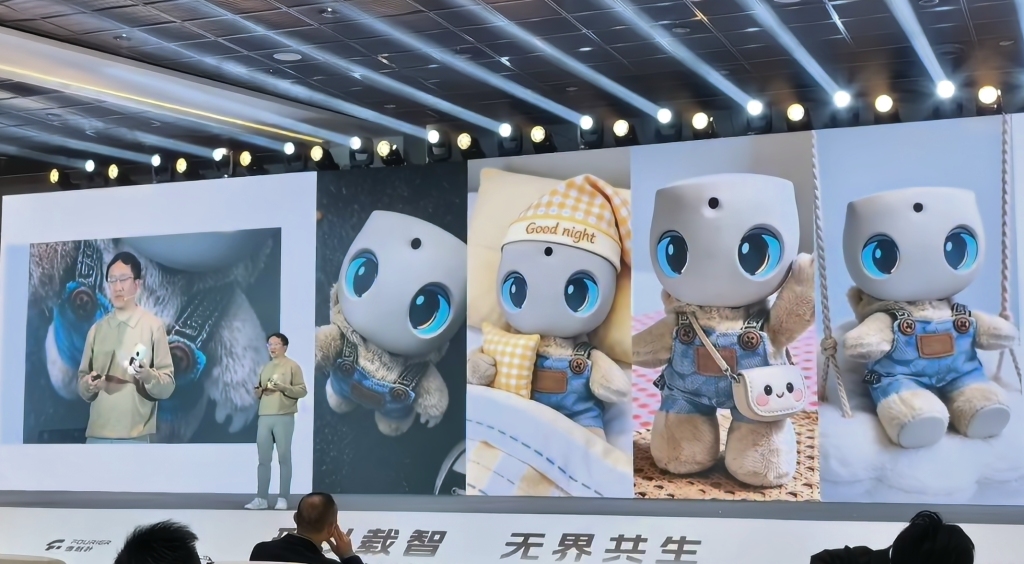“製造業回流”、“中國+1”戰略、“安全的第二選擇”……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供應鏈的話題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高度關注。
憑藉世界上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製造業體系,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地位。但與此同時,隨著美國對華貿易戰、科技戰的全面升級,美國層層加碼的“脫鉤斷鏈”政策也對中國製造業帶來了挑戰。
在此背景下,中國科協智能製造學會聯合體副所長、工信部智庫專家林雪萍在《供應鏈攻防戰》一書中提出,供應鏈是一種隱形國力,它關乎企業生存,關乎國力較量,也關乎民生。“供應鏈已然超越以往,成為企業與國家的角力場。”
他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國家參與的力量越來越顯著,中國企業的供應鏈組織方式也需要重新設計,以在全球市場應對國家級的角力。他呼籲建立一個系統性的公共支撐平臺,為企業提供金融、情報、物流等多方面的配套服務,以保護它們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
供應鏈安全成為企業重要考量
《21世紀》:近年來,全球化不斷遭遇逆流。在新冠疫情、俄烏衝突、能源危機、地緣政治危機等重重挑戰之下,你怎麼看經濟全球化的未來走向?過去,全球供應鏈發展主要由效率驅動,如今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即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全球化1.0時代,供應鏈是跨國公司最重要的武器,它們利用供應鏈在全球尋求最好的專業分工。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關注的重點是效率和成本,這也是全球化1.0的重要特徵,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超級工廠。但從2018年開始,很多西方國家逐漸強調供應鏈安全,推動世界進入全球化2.0時代。從新冠疫情開始,安全因素被進一步放大,很多國家開始思考口罩這樣的戰略物資是否應該本地化,而不是全球化。2021年前後的“晶片荒”導致傳統汽車產業受到巨大干擾。許多企業家在重新思考供應鏈是否應該集中在一個地方。隨著地緣政治因素被不斷放大,安全因素在企業供應鏈佈局中的優先順序也被大幅提高,成為效率和成本之外的關鍵考量因素。
從全球化1.0轉向全球化2.0
《21世紀》:你在書中指出,過去,在全球化的演變過程中,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超級工廠模式,中國供應鏈成為全球化運轉良好的基石,美國和中國則是塑造這一格局的關鍵力量。現在,這一模式正在經歷巨大挑戰。在從全球化1.0到全球化2.0的轉變過程中,中國和美國的角色有怎樣的變化?
在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1.0中,中國和美國是兩個相當重要的力量,它們在全球尋找讓效率最大化的供應鏈。雖然亞洲四小龍也有專業化的分工和產業遷移,但它們的發展受限於自身的經濟體量和勞動力規模,直到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後,憑藉縱深的市場和大規模的勞動力以及原有規劃體系齊全的基礎,成為重要承接之地,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中國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美國也通過這種結合將德國、日本、英國等國遠遠地甩在身後。
在全球化2.0中,目前來看,規則的設計仍然由美國主導,它希望將更多工廠分散出去,在中國之外形成新的製造基地,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美國存在更加明顯的競爭關係。然而,二者仍存在非常強的依賴。對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來說,中國仍然是重要的消費市場,而且美國的許多產品也依賴於中國的製造能力。因此,美國一方面想將產業遷移,另一方面又對中國保持依賴,這種關係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存在。
東南亞和印度各具優勢
《21世紀》:2023年,墨西哥取代中國成為美國第一大進口國。美國的產業回流政策對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中國供應鏈的向外遷移有哪些特點?
首先,這一輪產業遷移現象主要由外企拉動,而最大影響因素與地緣政治風險有關。談到成本問題,我們在產業中存在一種現象,即產業溢出。例如,低端產業結構會由於成本原因溢出到東南亞和南亞等地區。雖然很多時候這種溢出與低成本有關,但現在情況不同,產業遷移疊加了對供應鏈安全因素的考量。在這輪之前,有些遷往越南的工廠(既有中國工廠,也有外企工廠)離開那裏,比如,三星的電冰箱生產基地離開了越南,最終回到了韓國本土,這表明成本並非產業鏈轉移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越南的勞動力成本與中國相比並不低,而且它無法滿足企業對技能的要求。在很多越南工廠,企業需要派駐大量中國的技術人員,這也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此外,從供應鏈連接力的角度看,海外顯然比不上中國。
從供應鏈的角度看,越南、印度或者墨西哥目前無法完整替代中國。例如,越南的供應鏈仍然非常依賴中國,特別是在服裝和機電方面,這使得越南對中國有巨額的貿易逆差,而對美國有大量的貿易順差。這表明越南需要從中國進口中間產品,然後在本地裝配後向美國出口。在印度和墨西哥也是類似的情況。按照美國對供應鏈的設計邏輯,他們希望逐級把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地方,長遠來看,這對中國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如何留下跨國企業的供應鏈?
《21世紀》:你在書中說,美國對中國有兩種圍堵方式:一種是“脫鉤斷鏈”,另一種是“調虎離山”。能否展開談談?
“脫鉤斷鏈”是指不僅不售賣晶片等產品,還會按照價值觀形成聯盟,例如與荷蘭、日本等國聯合,對中國半導體裝備進行限制——這三個國家的半導體裝備占全球的80%。由於中國供應鏈的連接力具有很大的韌性,美國把之前“脫鉤斷鏈”的說法改為“去風險”,雖然表達方式溫和了一些,但推動方式仍然是“去中國化”。因此,美國會要求提高供應鏈的產地屬性,以電動汽車為例,要求動力電池必須在北美生產,這就迫使很多公司在中國之外建立新基地。
近年來,歐美商界廣泛討論的“中國+1”(China Plus One)供應鏈重組策略對跨國企業的影響非常大。這裏有兩點:第一個是地緣政治風險,第二個是在很多地方性貿易關稅下,企業不得不將工廠轉移到海外去。當它轉移到海外去時,它會邀請它的供應商跟它一起調整,以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這就是我所說的“釜底抽薪”,連鍋和柴火都轉移到另一個灶裏。
《21世紀》:中國製造需要應對一個新命題,即如何留住那些“長腿溜走”的跨國企業供應鏈。面對競爭,中國需要如何應對?
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跨國企業家的信心,進一步提升供應鏈的效率。隨著全球化2.0的推進,美國希望在中國成熟供應鏈之外再新建一條平行供應鏈。我認為,未來必然是平行供應鏈的競爭。當前,新的供應鏈仍處於生長階段,未來能否高效運轉仍未可知。因此,我們仍然需要按照自己的節奏,提升供應鏈的效率。未來,我們也許會讓更多轉移出去的企業回到中國。
中國企業應以“合成營方式”再出海
《21世紀》:按照你的預測,世界各地的“分佈式工廠”將開始繁榮。這給中國製造“再出海”帶來了哪些新的挑戰?
目前面臨的問題是不能僅依靠產品出海參加全球貿易和分工,而是需要將供應鏈能力出海,用這種方式重新參與新的全球化,在全球化2.0時代繼續佔據主動。因此,將這種現象稱為中國製造“再出海”。
當前,全球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和本地化要求增加了企業出海的風險,例如,中國企業在印度電子產業遇到的各種事情。面對複雜的局面,我們希望中國企業能夠採用供應鏈“合成營”的方式出海。所謂“合成營”,是一個軍事術語,意思是將原來高級編制才會有的兵種,如炮兵、防空兵等下沉到營級作戰單位。各部分各司其職、相互配合,讓原本只承擔某方面作戰能力的營級作戰單位,擁有了全面且獨立的作戰能力。
企業在出海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例如金融和物流方面的跟隨。例如,對汽車產業來說,在印尼這個全球第四大人口國,日本車系佔據了95%的市場。這是因為日本在全球佈局產業從來不是生產基地的轉移,而是一個綜合性的工業體轉移,採用了類似於合成營的方式,將供應鏈跟金融、物流、法規等一起打包進入。
在中國企業新一輪出海中,我們不僅需要製造出產品,還需要考慮物流、金融和文化等因素,將它們打包在一起。中國製造再出海是再次主動擁抱全球化的歷史性進程,中國應該建立一個系統性的公共支撐平臺,讓企業心無旁騖地做好核心事務,保護好它們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
來源:21經濟網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