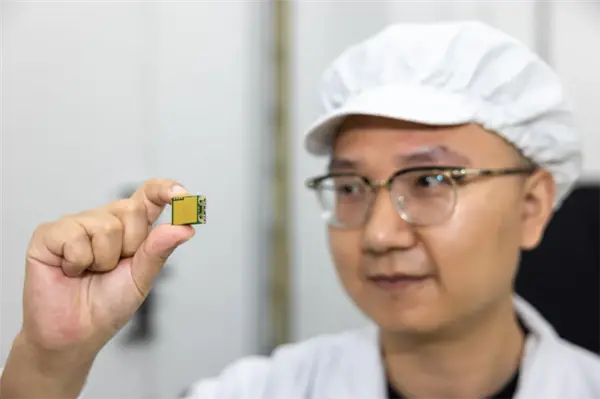山東最大民營企業、電解鋁及紡織巨頭魏橋創業集團,是中國電力發展史上十分特殊的存在。由其創建的“魏橋模式”通過自備電廠、自建電網,平均電價水準比國家電網低1/3,降低企業自身用電成本的同時兼顧周邊企業和居民用電用熱需求,但也因此引發關於自備電廠合法性及供電體系的大辯論。
10月17日瞭解到,在長達26年的孤網運行之後,魏橋集團已接入國家電網,兩者的關係在經歷多年積怨和對峙之後,迎來破冰。
據國網山東電力公司披露,10月15日,國網山東電力董事長、黨委書記林一凡會見魏橋集團董事長張波一行。雙方表示,此次會見恰逢雙方合作實現歷史性突破的重要節點。林一凡表示,電網公司認真落實山東省委省政府關於魏橋集團孤網接入公網要求,“超常規建成魏橋部分負荷、機組接網工程,結束了魏橋孤網運行歷史,助力魏橋降低煤炭消耗總量、更大力度消納全省綠電。”7月9日,魏橋3臺66萬千瓦機組正式並網,8月4日實現100萬千瓦負荷接入公網購電。
除了“山東首富”、“亞洲棉王”、“鋁業大亨”等頭銜之外,已故的魏橋集團創始人張士平曾被外界稱為“唯一敢與國家電網叫板的人”。但據澎湃新聞觀察,魏橋模式的出現有其複雜的歷史與體制背景,是電網企業、地方政府和企業在特殊歷史時期相互平衡、妥協的產物。時至今日,無論從電力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火電能效及環保標準的不斷提高還是從企業自身的發展需求來看,自備電廠已經失去肆意生長的土壤。
魏橋自備電廠:始於無奈的歷史產物
魏橋集團的前身是成立於1951年的鄒平縣魏橋棉紡織廠,由鄒平縣供銷合作社聯合社出資設立。發展至今,其已成為擁有國內外18個生產基地、10萬名員工、2800億元總資產,集紡織、印染、服裝、家紡、熱電等產業於一體的特大型企業。2012年以來,魏橋集團連續13年入選世界500強,2024年位列第175位——這一排名超過了招商銀行、浙江吉利集團和臺積電。
在企業壯大過程中,由於電、汽能源全部自給,與當地工業電價相比,自發電成本優勢明顯,創造了可觀利潤。更重要的是,依託自備電廠的低成本優勢,魏橋的商業版圖不斷擴大,熱電業務也逐漸成為其利潤的重要來源。
2016年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發佈的一篇跟蹤評級報告曾令公眾得以一窺自備電廠的巨大優勢。
報告披露,魏橋集團2013年-2015年自發電成本分別為0.29元/千瓦時、0.21元/千瓦時、0.18元/千瓦時,2016年1-3月,自發電成本僅為0.17元/千瓦時。除了給自身的紡織、鋁業企業供電外(自用比例在34.76%左右),魏橋熱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還用於外銷,經當地政府准許,應用自有管線銷售給非合併範圍內的關聯企業、周邊村鎮和企業,其電價比國家電網低三成以上。
燃煤自備電廠的身份常面臨“合法性”的質疑。但回顧當年,魏橋集團的自建電網、自行供電,其實是無奈之舉。
上世紀90年代,全國性電力緊缺,隨意拉閘限電現象嚴重影響了紡織企業的生產秩序,並使生產成本大幅攀升。據《英才》雜誌報導,在自建電廠之前,魏橋系一直以燒鍋爐的形式生產紡織所需的蒸汽,經濟性差且不環保。熱電聯產的好處在於,在生產電力的同時還能夠產生紡織工藝中所必須用的蒸汽。
1999年9月28日,魏橋第一熱電廠建成投產,裝機容量為7.8萬千瓦。但第三天上午,魏橋方面就接到淄博電網通知,要求其必須從大電網中解列(指電力系統受到干擾,其穩定性遭到破壞,發電機和電力系統其他部分之間、系統的一部分和系統其他部分之間失去同步並無法恢復同步時,將它們之間的電聯系切斷,分解成相互獨立、互不聯繫的部分,以防止事故擴大造成嚴重後果。)考慮到孤網運行的風險,魏橋方面一時不敢答應解列。但淄博電網同時對鄒平縣政府提出了警告。
“縣長親自找到我,說淄博電網警告了,如果魏橋的自備電廠不解列,將對整個鄒平縣的用電安全產生威脅。”張士平曾對媒體回憶稱,縣長登門令其想法突變,他告訴縣長,一定會爭口氣,要變壓力為動力,同意解列,“我當時想,淄博電網叫我下網,他以後就管不著我了,我的發電量肯定還要擴大,以後他求我上網,我也不上了。”此後的故事廣為流傳,魏橋集團的自備電廠不但為本集團旗下企業供電,還通過自建電網向當地其他企業供電。這一模式下,魏橋的紡織和鋁業業務快速擴張。
實打實的價格優勢吸引了魏橋鎮周邊其他城鎮的民營企業到魏橋集團來買電。“我不是吹牛,我們從來沒有出過停電事故。” 張士平曾對外表示。
有電解鋁業內人士曾對澎湃新聞分析稱,“魏橋、宏橋(指魏橋的電解鋁板塊上市公司中國宏橋)的優勢,就在電力。電解鋁不是什麼高科技行業,就是看誰成本低。”其介紹,電解鋁成本主要分三塊,電力成本占到40%到50%;氧化鋁、陽極材料等,大概是30%;人工加財務,大概5%到10%左右。“真正拉開差距的,就是電力成本。1度電,如果相差0.1元,反映到電解鋁的成本,就是每噸1500元-2000元。”
該人士還表示,“一般從電網購電,大電用戶每度電成本大概0.35元,正規的自備電廠,即交各種附加、基金的,大致可以降低到0.25元/度。魏橋自備電廠、又自建電網,還各種熱電聯產,同時不用交各種附加、各種基金,不用管各種交叉補貼,估計實際成本可以低到0.2元/度,這就是巨大的優勢。反映到產品上,就是利潤。”
自備電廠紅與黑
“以魏橋電網的效益和價格來看,大系統的效率比小系統還要高,因此(大電網)電價應該更低才對。”有資深電力人士曾對澎湃新聞評述道,魏橋模式是非常鮮活的例子,電力行業大可以將魏橋終端平均用電效率作為參照系,大電網完全有理由超過它。
魏橋模式之所以備受推崇,是因其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電價的“真相”。
此前有分析稱,在山東,每一度電中含農網還貸資金2分錢、三峽工程建設基金0.7分錢、城市公用事業附加費1分錢、庫區移民後期扶持資金0.88分錢、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0.1分至0.4分錢等一系列費用,而用自備電廠發電的魏橋集團無須承擔這些。加上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等,才有了魏橋集團的電價比國家電網低1/3的現實。
但魏橋模式自誕生之日起便充滿爭議。支持者認為其代表了電力市場化的方向,反對者則指責稱,魏橋模式“不合法、不安全、不環保”,沒有承擔社會責任、是“違法供電”。
曾幾何時,各地民企和媒體蜂擁至山東鄒平,欲效仿魏橋模式。比如2011年底,新疆相關部門官員到魏橋鎮調研,希望在新疆複製魏橋模式。
較為普遍的業內觀點是,魏橋模式僅是局部個例。充足的資金和穩定的用電量、能拿到相應的專案、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幾項因素缺一不可。長期缺電逐漸消失後,自備電廠常因“未公平承擔社會責任”、“管理混亂”、“加劇環境污染”而遭到詬病,游離於合法與違規的邊界之間。
據當地媒體報導,歷史上魏橋集團曾與國家電網山東電力公司產生過多次激烈衝突。雙方規模最大的一次武鬥發生在2009年,地點在山東省惠民縣李莊,衝突的焦點就在於魏橋集團欲將自己的電輸往惠民縣。2012年中國家電網與魏橋集團達成協議,魏橋的餘電在滿足廠區周邊商戶用電後重新併入山東電網,實現互利共贏。
燃煤自備電廠的治理敏感而複雜。2016年開始,史上最嚴自備電廠整治風暴席捲而來,自備電廠迎來強監管時代。
作為落實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配套檔之一,2015年11月公佈的《關於加強和規範燃煤自備電廠監督管理的指導意見》指出,企業自備電廠自發自用電量應承擔並足額繳納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農網還貸資金、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大中型水庫移民後期扶持基金和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依法合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以及政策性交叉補貼,各級地方政府均不得隨意減免或選擇性徵收。
國家發改委在解讀上述檔時表示,燃煤自備電廠由於專業化運行管理水準不高,監管難度大等原因,普遍存在能耗水準高、環保排放不達標、環保設施不完善等問題。
2017年5月,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下發《關於開展燃煤自備電廠規範建設及運行專項督查的通知》,並會同工業和資訊化部、財政部、環境保護部等部門赴新疆、山東、內蒙古、江蘇、廣西、甘肅等地開展了燃煤自備電廠規範建設及運行專項督查。督查的主要內容,包括燃煤自備電廠的基本情況、燃煤自備電廠承擔社會責任情況及燃煤自備電廠的達標排放情況。
上述開展專項督查的省份中,許多屬於自備電廠在發電裝機總量中所占比例較高。比如,截至2016年底,新疆自備電廠裝機容量已居全國第一,發電量占新疆電網用電量6成以上。截至2015年底,山東全省發電裝機總容量達到9779萬千瓦,其中自備電廠裝機3043萬千瓦,自備電廠裝機容量占比為31.12%,自備機組全年發電量達1699.8億千瓦時。
2018年,“史上最嚴燃煤自備電廠整治方案”徵求意見。據中國能源報報導,國家發改委彼時收到了魏橋及另一民營鋁電龍頭信發集團對於徵求意見稿的回饋——“魏橋集團16萬人、信發集團8萬人下崗給你們看”。
政府性基金補繳問題是各方拉鋸的焦點。彼時有業內人士分析,很多自備電廠自發自用,基本不繳納政府性基金,這是造成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儘管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以及國家能源局等相關部門多次發文要求自備電廠嚴格按照規定上繳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但實際繳納情況不容樂觀。
2018年5月公佈的《山東省貫徹落實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督察回饋意見整改方案》顯示,環保督察發現,2013年以來,魏橋集團違規建設45臺火電機組,總裝機容量1689.5萬千瓦,濱州市始終未採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根據相關整改措施清單,魏橋集團45臺違規建設的機組中,33臺允許取得環評備案手續後繼續運行,另外12臺機組中,4臺停建、8臺停運。
國家能源局日前印發的《關於加強用戶側涉網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省級電力管理部門統籌梳理並認定本地區涉網用戶範圍,重點覆蓋大負荷用戶、電能品質敏感型用戶、源荷混合型用戶、負荷聚合類用戶及自備電廠等類型。對於自備電廠,必須納入統一調度管理,嚴格落實涉網試驗、保護定值校驗等規定。
來源:中國澎湃新聞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