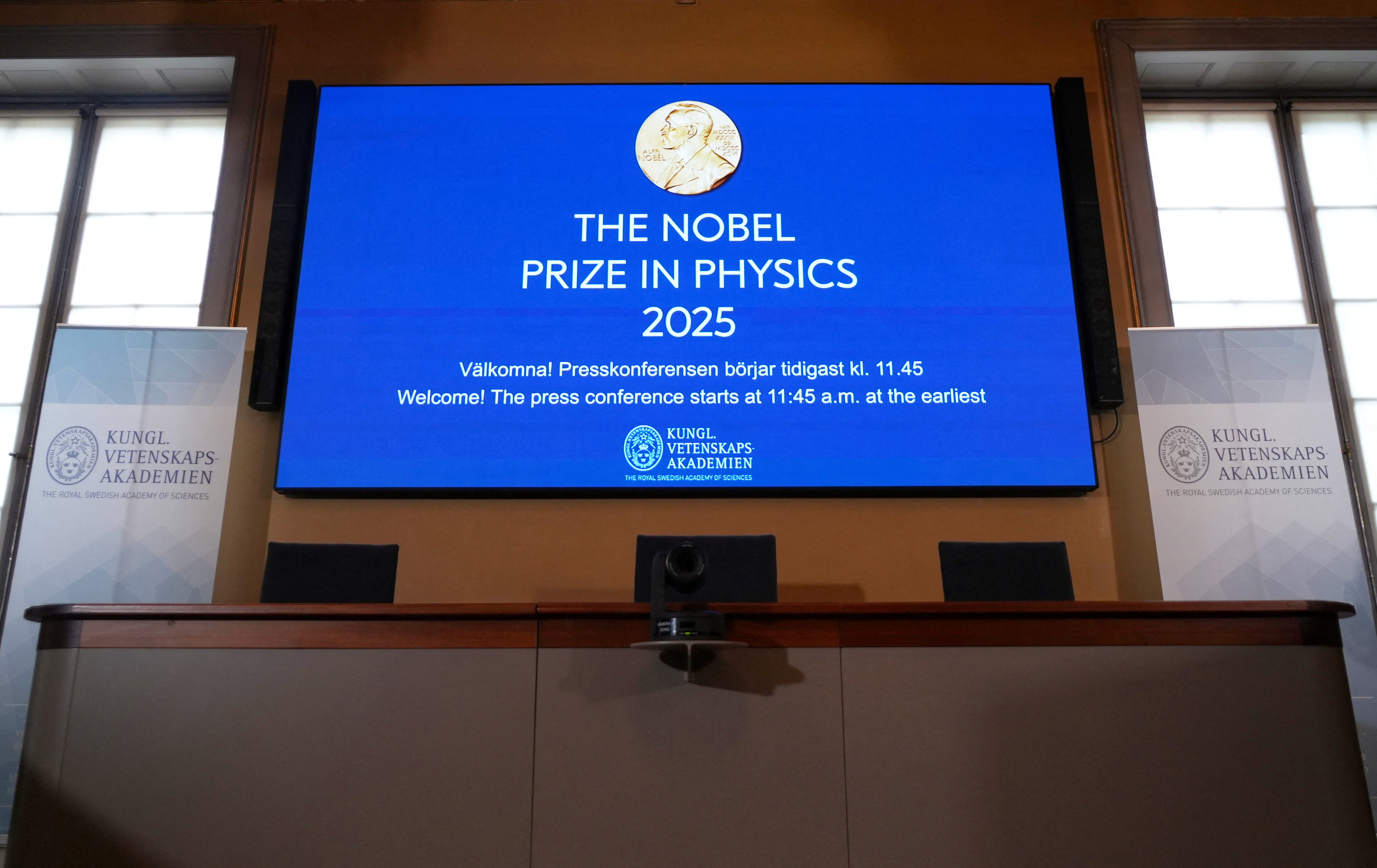“當蒸汽機車出現在倫敦街頭時,遭到了坐馬車貴族的嘲笑,然而今天馬車只是一種旅遊專案。”4月21日,在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相關論壇上知名導演黃建新這樣形容AI對電影行業的影響。某種程度上,黃建新算一名“傳統”導演,他的作品包括《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
同一場合,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表態,AI有可能降低成本,甚至成為盈利關鍵。“即使降低20%的製作成本,對行業都有巨大推動。因為中國電影行業內容生產環節整體是虧損的,如果我們能夠降低20%成本,有可能會變成盈利。”他稱。
AI的確在飛速發展。2月16日,OpenAI發佈首個AI視頻生成模型Sora,能夠生成長達1分鐘的高清視頻,同時保持極高一致性,並可理解和模擬物理世界。3月,月之暗面宣佈其對話式AI助手產品Kimi智能助手現已支持200萬字的無損上下文輸入。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國產大模型Kimi文字能力全面達到GPT-4水準。
眼下,AI已經深入到了創作環節。
“拯救者”
王長田將AI抬高到了行業生存的關鍵要素。他表示,初步預計AI會讓電影製作效率提高30%或者以上,隨之而來的是製作成本降低20%。“尤其在動畫電影方面,因為動畫電影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產能不足,生產效率低下。”王長田說。
華納兄弟探索院線發行(亞太區)高級副總裁庫爾特·瑞德認同上述觀點,他表示,過去主要的好萊塢作品或許需要幾年的製作時間,現在製作週期縮短了約20%,電影公司發行效率有很大提升。“以前一年可能製作8-9部作品,現在是12-15部作品。”庫爾特稱。
基於此,王長田在光線傳媒強推AI。“公司的AI應用比重會越來越高,至少在動畫製作領域,我們要求動畫製作的每個環節都要有意識地應用AI,哪怕做得不好也要嘗試。”他介紹。
但不能回避的問題是,當前AI發展水準尚未達到電影水準。“AI的清晰度、想像力、人物和場景一致性方面還遠遠達不到電影需求,因此只能應用於一些基礎性前期環節。比如電視劇、網劇更多是再現現實,電影是在現實的基礎上超越現實,不同的產品對AI技術的使用需求不一樣。目前,AI在再現現實、描述現實的時候起到的作用比較大。而涉及超越現實時,僅能在動畫的一些創作環節有幫助,但對創意、想像力環節沒有太大幫助,所以AI有一定的局限性。”王長田表示。
不過,當前中國電影行業依舊陷於資金困局,AI卻是行業虧損局面下為數不多的出路,至少A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成本問題。業績預報顯示,2023年博納影業預計虧損3.6億—5.6億元,2023年華誼兄弟預計虧損4.6億—6.9億元。
在北京國際電影節期間,壞猴子影業CEO王易冰坦承,這兩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兩個字,缺錢。壞猴子影業出品專案包括《我不是藥神》《孤注一擲》等頭部作品。
導演張末深有同感,“從去年開始我也有這種感受,就是拍大片的機會少。”張末執導作品《拯救嫌疑人》於2023年年末上映,她的父親是知名導演張藝謀。
投資回報的不可控,讓資本不敢進入電影市場,拍攝模式的非標化讓成本控制顯得飄渺。因此,電影專案特別是中等專案募資更難。
“顛覆者”
當AI深入到創作領域時,業內態度就更曖昧了。
在美國,電影行業對人工智慧日益增長的恐懼導致了好萊塢六十多年來最大的勞資糾紛。編劇們要求電影公司承諾不使用AI生成劇本或訓練所謂的大型語言模型,這種模型能根據他們的作品大量生成各種變化形式。他們還想確保只有人類才能獲得編劇署名。演員們亦擔心自己的面孔被濫用。
放眼國內,目前AI尚未在內容端造成顯性衝突,但也可能帶來顛覆性影響。
愛奇藝創始人、CEO龔宇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分析,AI深入內容端可能給新人入行帶來“災難性”影響。“以後的導演、製片人、編劇可能不需要年輕人了,跟機器對話就夠了,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輸入到機器裏,機器可以幫助人們動筆寫出文字、畫出分鏡,甚至選角。”他說。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年輕人可以借AI超車。“此前年輕人沒有機會創作一個完整作品,現在通過生成式人工智慧,可以寫出劇本,生成一個完整作品,同時不需要很多錢,或許50萬元就能拍出一個類似500萬甚至5000萬投入效果的好電影。”龔宇表示。
黃建新表示,Sora的出現不是物理世界原本的面貌,它是迎合了人類幻覺需求的面貌。“從這點來看,它依舊是人類幻覺外延,而不是本質對抗。”黃建新表示。
基於此,黃建新認為,這是年輕人的機會,因為他們沒有負擔,很容易跟AI擁抱融合。
黃建新還舉例,當電視出現時,所有人都認為電影要衰落。但後來電影技術革命,IMAX、杜比聲音完整性和空間表現能力再次與電視拉開了距離,人們重新回到電影,保持了電影蓬勃的狀態。AI是一個好東西,我們跟它建立良好的關係只會對我們有好處。
和美國同行一樣,演員們對AI也有著自己的體悟。“如果有一天AI能複刻出人類的複雜眼神,或許演員這個職業就到頭了。至少,目前看這個情景還很遙遠。”有知名演員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感慨。
來源:21經濟網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