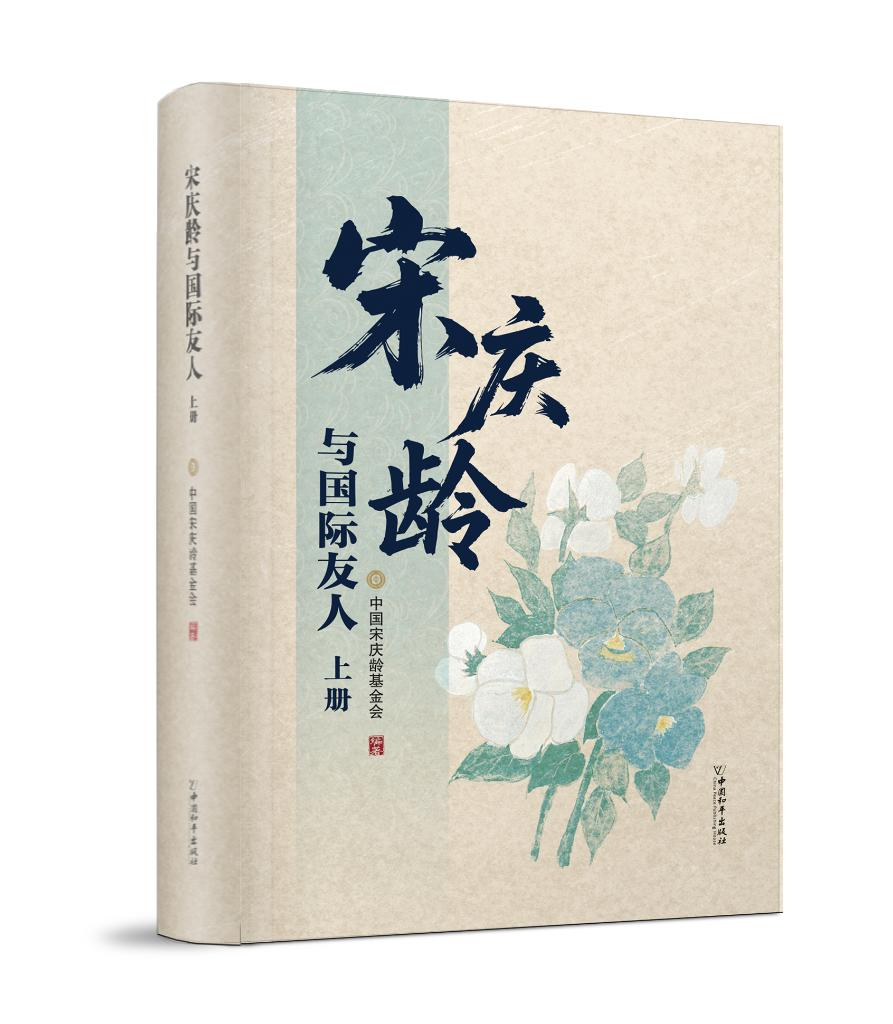中國當代文學外譯中“文學性”的再現
——以餘華《在細雨中呼喊》中語言變異的英譯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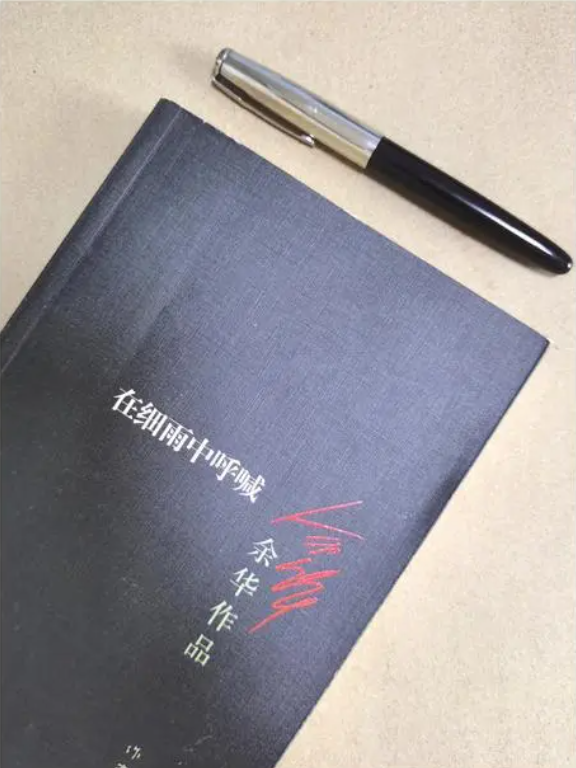
本網綜合許宗瑞 1,2,陸國玟 2報導
(1. 上海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上海 201620;2. 安徽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文學性”的再現是中國當代文學外譯乃至中國文學外譯的一個重要命題。利奇在《英詩學習指南:語言學的分析方法》(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一書中總結的英語詩歌的八種語言變異情況,為考察以小說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性及其在翻譯中的再現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參考。餘華小說《在細雨中呼喊》具備利奇提出的全部八種語言變異的情況,但是對小說英譯本的檢視顯示,譯者在面對原文語言變異的翻譯處理整體而言重視不夠,譯文美中不足。
關鍵字:中國當代文學外譯;文學性;語言變異;《英詩學習指南: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在細雨中呼喊》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395(2023)05-0035-06
中國當代文學外譯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翻譯界、文學界、出版界等諸多領域都十分關注的話題,因這項工作承載了較多期待,取得了一系列階段性成績,但同時也面臨不少現實挑戰。作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當代文學外譯被寄予了較大期望,是增進中外人文交流、促進國際社會認識和瞭解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管道。新世紀以來,在“走出去”方略的推動下,莫言、餘華、閻連科等中國當代作家屢獲國際文學大獎,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版權輸出節節攀升,科幻文學、網路文學等文學類型在對外譯介和海外傳播中嶄露頭角。但是,中國當代作家受到的關注總體不足,作品得到的評價尚不理想,海外讀者參與作家和作品討論交流的積極性也有待提升 [1]。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始終處於相對較低的地位,產生的影響仍比較有限。有學者指出,文學地位的建立和提升,首先是作品需具有較高的文學品質和文化內涵,但同樣重要的是如何闡釋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2]。因此,如何妥善處理和再現作品的文學性是中國當代文學外譯工作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文學性、語言變異與中國當代文學外譯研究
“文學性”(literariness)是學界普遍關注且長期討論的一個論題。這一概念源於俄國形式主義學“文學性”(literariness)是學界普遍關注且長期討論的一個論題。這一概念源於俄國形式主義學派,最早可追溯至該學派代表人物羅曼·雅各布遜(Roman Jakobson)20 世紀初的有關主張。雅各布遜認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不是籠統的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一部作品成其為文學作品的東西,也就是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形式特徵 [3]34。20 世紀末美國解構主義學者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論述“文學的本質”時也指出,文學是語言的“突出”,是語言的綜合,是虛構,是審美對象,是互文性的或者自反性的建構 [4]28-35。兩位學者在 20 世紀一頭一尾發出了遙相呼應的聲音,為近一個世紀文學研究的精神歷險描畫出一個“蛇咬尾巴”式首尾銜接的圓圈,其中心就是文學性問題 [5]。雅各布遜和卡勒的上述主張都涉及語言的變異:在前者看來,文學 性就蘊藏於作家對日常語言加以變形、強化甚至扭 曲中,對普通語言實施有系統的破壞[6];在後者看來, 文學的本質首當其衝的是,一種語言表達的違反常 規或者某種特徵的凸顯 [7]10。因此,作家往往使用偏 離常規的表達手法,實現陌生化、前景化的效果, 製造作品的文學性 [8] 。
關於文學性與語言變異之間的關聯,傑弗 裏·N·利奇(Geoffrey N. Leech)與雅各布遜、卡 勒在很大程度上可謂不謀而合。利奇在 20 世紀 60 年代出版的專著《英詩學習指南:語言學的分析方 法》(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下文簡 稱《指南》)中,總結了英語詩歌中常見的八種語 言變異(linguistic deviations)情況,包括辭彙變異、 語法變異、語音變異、語相變異、語義變異、方言 變異、語域變異、歷史時代變異 [9]42-55。這些變異是 詩歌之所以成其為詩歌、具有詩意和文學性的關鍵。 有學者將利奇的這一主張引入中國當代小說翻譯研 究,以閻連科多部小說英譯為研究對象討論了原作 中語言變異性表達在英譯本中的再現情況 [10] 。該研 究為當下中國當代文學外譯工作和外譯研究提供了 新的借鑒和啟示。但是詩歌和小說畢竟不同,英國 文學和中國文學也存在不小差異,該研究的有效性 還有待進一步驗證。鑒於此,本文以另一位中國當 代作家餘華為例,聚焦餘華小說《在細雨中呼喊》[11] 原文及其英譯本Cries in the Drizzle[12] ,希望繼續從 語言變異英譯這一視角探討中國當代文學外譯中文 學性的再現問題。
二、餘華《在細雨中呼喊》中 語言變異的英譯
《在細雨中呼喊》是餘華第一部長篇小說,發 表於 1991 年。這部小說標誌著餘華文學創作的日趨 成熟,同時也預示了餘華後續作品的諸多主題和故 事情境。法國《文學雙周》認為,《在細雨中呼喊》 使得餘華成為近二十年以來中國文壇最為閃耀的明 星之一 [11]200。該小說譯者是美國漢學家、翻譯家白 亞仁(Alian H. Barr)。美國《出版商週刊》對白亞 仁英譯本的評價也頗高:“完美地捕捉了一個處於 變革邊緣的群體的興衰”[13] 。但是如果從原著語言 變異英譯的角度審視,該譯本還是有些美中不足。
(一)辭彙變異
辭彙變異(lexical deviation)是利奇在《指南》 中總結的第一種語言變異的表現。利奇指出,創造 新詞(neologism)是詩人(及記者等)為超越日常 語言資源經常採取的一種手段,而且英文中很多已 廣泛使用的詞語都源於之前詩人在詩歌中的創造, 譬如斯賓塞創造的新詞“blatant”,莎士比亞創造 的“assassination”,彌爾頓的“pandemonium”, 蒲柏的“casuistry”[9]42。這一現象在中國當代小說 中也十分普遍。每個時代的小說家都會選用新詞注 入自己的小說,我們時代也不例外,有意識地吸納 新詞是寫作者的本領 [14] 。在《在細雨中呼喊》中, 餘華也屢屢創造新詞或舊詞新用,以增強語言表達效果。
例 1:比起這樣的場面來,我祖母的婚禮 不過是杯中之水。[11]140 譯文:Compared with this, her wedding was a nonevent. [12]154 例 2:我祖父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孝子,他 不忍心看著我曾祖母扭著小腳在路上艱難行走, 於是他始終背著母親,滿頭大汗氣咻咻地在那 些塵土飛揚地路上,跟隨著逃亡的人流胡亂奔 走。[11]150
譯文:Being the devoted son that his era expected him to be, he could not bear to see my great-grandmother lurching down the road in her bound feet, so he carried her on his back the whole way, sweat pouring down his face, panting for breath, following the refugees as they fled helterskelter along dust-swirled roads. [12]166
例 1 中“杯中之水”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見景象, 但在文學作品的字裏行間並不常見。結合原文上下 文語境,可知其涵義為祖母的婚禮像杯中之水一樣 平淡無奇。這一新奇表達能帶給讀者新鮮的閱讀體 驗。但是譯者並未將杯中之水的意象譯出,而是意 譯為“a nonevent”,雖然原文資訊得到了傳達,但 文學性損失了不少。同樣,例 2 中的“氣咻咻”也 非漢語中的常用辭彙,用在此處是描述“我”的祖父孫有元背著曾祖母逃亡時經歷的艱辛。“咻咻” 為擬聲詞,描繪了祖父當時氣喘吁吁的模樣。譯者 此處的處理“panting for breath”,也是將重心放在 了語義的傳達上,也未採用英文中的任何新奇表達 或擬聲詞,使得原文表達生動性有所降低,詞語創 造性使用的痕跡不復存在。
(二)語法變異
語法變異(grammatical deviation)是《指南》 中總結的第二種語言變異形式,主要包括詞法變異 和句法變異。利奇指出,前者在英文詩歌中十分少 見,因此他對語法變異的論述主要圍繞後者展開。 句法變異的主要表現之一是,刻意打破句子的表層 結構(surface structure),但同時不影響意思的傳 達,譬如採用“I doesn’t like him”“He me saw”等 類似語法上存在明顯問題的語句;其二,刻意打破 句子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採用如“a grief ago”等十分罕見的搭配,按照常理“grief”一詞的 位置上本該使用像“year”“day”“minute”等表 示時間的名詞 [9]45。在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中,這 種變異情況也比較常見。
例 3:船頭微微起伏著,劈開的河水像匕 首一樣鋒利地迅速後退。[11]138
譯文:The bow gently rose and fell, cleaving the river like a knife and propelling the water into rapid retreat. [12]152
例 4:這位我後來的母親整個身體就像是 一場綿綿陰雨。[11]190
譯文:It was as though, without exposure to sunshine, this second mother of mine was shrouded in a perpetual drizzle. [12]210
例 3 中“鋒利地”和“後退”搭配,屬於刻意 打破句子的深層結構,形容河水的流動速度之快。 譯文中譯者此處的處理為“propelling the water into rapid retreat”,“後退”的意思得到了保留,但“鋒 利地”消失不見。雖然譯文中使用了“rapid”一詞, 但原文的語言變異沒了蹤跡,陌生感大大降低。例 4 中將“我”繼母的身體比作“一場綿綿陰雨”, 意思是繼母身體虛弱,並且這樣的狀態持續很長時 間,一直沒有好轉。“身體”和“一場綿綿陰雨” 結合,顯然不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屬於刻意打破了句子的表層結構。此處譯者譯為“shrouded in a perpetual drizzle”,並且附加了“without exposure to sunshine”的說明,使得語義更加明晰,表達更加 順暢,但丟失了原文因語言變異產生的奇特效果。
(三)語音變異
利奇關於語音變異(phonological deviation)的 討論主要圍繞一些反常的發音情況,具體包括省音、 詞首非重讀母音省略、詞尾音消失等,以及行文中 為了押韻對個別單詞發音所做的一些調整 [9]47。在中 國當代小說中,語音變異主要體現在韻律、節奏的 變化,比如《在細雨中呼喊》的以下例句。
例 5:“要死就別吃,要吃就別死。”[11]178 譯 文:“If you’re going to die, don’t eat! If you’re going to eat, don’t die!”[12]198
例 6:“一個就打,兩個逃回家。”[11]153
譯文:“Beat one, flee two.” [12]170
例 5 是原文中“我”的父親孫廣才對瀕死的祖 父孫有元的呵斥。對話中“要”“就”“別”三詞 重複出現,並且“死”和“吃”與“吃”和“死” 在韻律上反復呼應(韻母“i”重複 4次),體現了“我” 父親對祖父的不耐煩和不孝。此處譯文的句型同原 文一樣對稱,兩個“If you’re going to…don’t…”構 成的結構前後呼應,但是原文“死”和“吃”反復 呼應的音韻效果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例 6 是“我” 的父親孫廣才在哥哥孫光平上學前要他記住的口令。 這一口令簡潔明快,朗朗上口。譯者在翻譯時的處 理“Beat one, flee two”整體也不拖泥帶水,很好 再現了原文的節奏,但“打”和“家”押韻的效果 同樣也是沒有得到再現。
(四)語相變異
語相變異(graphological deviation),又稱“書 寫變異”,是指偏離常規的書寫形式。利奇指出, 詩歌書寫形式的變化是語相變異的重要體現,比如 該用大寫字母時用小寫字母,該加標點符號時不加 標點符號,單詞之間該空一格時不空格等 [9]47。這種 變異情況在《在細雨中呼喊》中也能找到一些蹤跡。 例 7:這位已經死去的德國老人曾經說過:
——恐懼與顫抖是人的至善。[11]79
譯文:…and perhaps more akin to what Gothe intended when he wrote, “To shiver ismankind’s finest lot.” [12]88
例 8:接著是很細的聲音,像一根針穿過 針眼一樣穿過了我的耳朵,她告訴我,她要是 穿上潮濕的內衣就會—— “立刻死掉。” [11]190
譯文:Then I heard a sound so thin it was as though a thread was passing through my ear, the way it might pass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She was telling me what would happen if she wore damp underwear: “I’d be dead in a second.” [12]210
例 7 中冒號後餘華另起一段,再加破折號引出 德國老人歌德的名言。聯繫上下文可知,這句名言 位於“戰慄”章節的開端,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另 起一段是為了強調此句。而譯者在譯文中並未做出 同樣調整,上下兩句整體合併為一個段落,無法凸 顯這句話的分量,也無法體現其過渡效果。例 8 也 是如此。“立刻死掉”之所以換行並另起一段,旨 在烘托繼母和“我”說話時那種陰森的氛圍,同時 原文中也提到,聽到這句話的“我”嚇了一跳,因 為平時病弱的繼母在說這一句話時卻斬釘截鐵。這 裏另起一段雖不符合常規,但十分必要。而譯文並 未參照原文的處理方式,沒有體現原文的語相變異, 再現原文的表達效果。
(五)語義變異
關於語義變異(semantic deviation),利奇援引 葉芝的“非理性元素”(irrational element)以解釋 這一現象。利奇指出,詩歌往往是一種靈感中的荒誕, 人們常忽視詩歌的這一特點,譬如華茲華斯詩中的 名句“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the man”看似十分 荒謬,卻發人深省 [9]48。《在細雨中呼喊》中也存在 不少類似的非理性表達。
例 9:突然一股強烈的光芒蜂擁而來,立 刻扯住了他,可光芒頃刻消失,蘇宇感到自己 被扔了出去。[11]108
譯文:Suddenly a beam of light shone in and stopped him in his tracks, but the brightness instantly extinguished and Su Yu had a feeling of being hurled beyond its reach.[12]119
例 10:陽光是很想照到這裏來的,是山把 它半路上劫走了。[11]192
譯 文:The sun wanted to shine in my room, but on its way here the mountain abducted it. [12]212
例 9 中“光芒”和“蜂擁而來”結合十分反常, 但刻畫了瀕死的蘇宇對於陽光的渴望。在譯文中, 譯者直接簡化處理為“a beam of light shone in”, 即一束光照射進來,未能再現原文此處遣詞造句的 反常和精妙。例 10 是同樣對陽光充滿渴望的“我” 的繼母所說的話。餘華擬人化的表達“山把它半路 上劫走了”也是不合常理,但言外之意是繼母李秀 英對山擋住了陽光的不滿,對於陽光的渴望。此處 譯者的翻譯“the mountain abducted it”,則較好地 保留了原文擬人化的效果,再現了繼母語氣中的怨 哀。
(六)方言變異
方言變異(dialectal deviation),在利奇看來是 在寫作中融入社會性方言或地域性方言,此舉為各 種身份類型的作家普遍採用,例如斯賓塞在《牧羊 人月曆》中使用的諸如“hydeguyes”(一種舞蹈)、 “rontes”(小公牛)等方言土語,營造出一種質樸 無瑕的感覺和田園般的詩情畫意 [9]49。在翻譯時,文 學作品中的方言成分往往會給譯者帶來挑戰。因為 這些成分在作品中不僅傳達了一定的字面意義,而 且通常還有著相當重要的文體功能,具有獨特的藝 術效果 [15] 。在《在細雨中呼喊》中,餘華筆下不少 詞語也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
例 11:“我要是騙你,我就是狗娘生的, 狗爹養的。”[11]40
譯文:If I’m lying, then my mom’s a bitch and my dad’s a dog. [12]46
例 12:“我爹死了沒錢收作,我娘或者躺 在屋裏沒錢治病。做做好事吧,過幾天我就將 爹贖回去。”[11]147
譯文:“My dad is dead, and I have no moneyfor his burial; my mom is alive, but ill in bed at home with no money for treatment. Do a good deed, will you? I’ll redeem my dad in a few days’ time.” [12]162
例 11 中“狗娘生的,狗爹養的”源於“狗娘養 的”,後者是中國大江南北常聽到的一句俗語粗話, 在《在細雨中呼喊》的人物對話中也反復出現。例 12 中的“收作”為杭州、湖州等地方言,意為“收拾”,普通話中很少使用。在譯文中,譯者將“狗 娘生的,狗爹養的”譯為“my mom’s a bitch and my dad’s a dog”,不僅保留的原文中方言的意象,還再 現了原文對話的俚俗氣。但是“沒錢收作”譯者處 理為“no money for his burial”,方言的痕跡消失不見。
(七)語域變異
語域變異(deviation of register)是指語域混雜, 即同時使用應在不同場合才能使用的表達[9]50。語 域是語言使用場合或領域的總稱。語言使用場合或 領域可分為新聞語言、演說語言、廣告語言、課堂 用語、辦公用語等。如果不同場合和領域的語言混 雜,會產生奇特效果,《在細雨中呼喊》中也有類 似的例子。
例 13:他用自己不可動搖的權威,去恫嚇 那些膽小怕事的村民,警告他們誰要是窩藏菩 薩,一律以反革命論處。[11]170
譯文:He used his incontestable authority to intimate the weak-kneed villagers, warning them that anybody who tried to harbor a bodhisattva would be punished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12]188
例 13 中“他”是身為共產黨員的“隊長”, 此句的背景是隊長帶領民兵前去銷毀菩薩,旨在破 除村民的求雨迷信,讓村民相信人定勝天。隊長的 警告“一律按反革命論處”具有強烈的政治屬性, 是特殊歷史時期特定語境下中國的一句政治話語, 對違反者行為的定性是重罪。但是此處譯者翻譯為 “punished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對中國歷史 不太瞭解的英語讀者而言,可能意識不到原文此處 的隱含意義。而且在英美國家的語境中,“反革命” (counterrevolution)可能還是正義之舉,譬如 2021 年 11 月 14 日《華盛頓郵報》一則報導中就提到, 美國將繼續在古巴掀起反革命的大潮。 (八)歷史時代變異 歷史時代變異(deviation of historical period), 是指作者使用超越自身所處的歷史時代的語言,比 如古語,進行自由創作 [9]51。這種語言變異情況在《在 細雨中呼喊》中也有運用。
例 14:這個滿嘴先天下人憂而憂、後天下 人樂而樂的秀才,一聽要砍他家的大香樟樹, 就跟掘他的祖墳一樣氣得暴跳如雷,他完全忘 記了自己的滿腹經綸,面對那幾個前來商量的 人,他用農民的粗話破口大罵。[11]144
譯文:A licentiate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e was much given to pontificating about the scholar’s obligation to be first to worry about the world’s problems and last to enjoy the world’s pleasures. But when he heard that there was a plan afoot to fell his family’s camphor tree, he was just as incensed as if they were proposing to dig up the ancestral tombs. [12]159
例 14 中餘華用範仲淹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來形容祖父孫有元的岳父劉欣之, 與後文的“破口大罵”形成鮮明對比,極具諷刺意 味。譯者在翻譯原文的“秀才”時採用了“licentiate” 一詞,該詞源於中世紀時期的拉丁文“licentiatus”, 可向讀者傳達“秀才”是中國古時的一種特殊身份 或頭銜。但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的譯文“to be first to worry about the world’s problems and last to enjoy the world’s pleasures”,譯出了原文 的涵義,但古文古樸典雅的風格未能得到再現。
三、結語
文學性的再現是中國當代文學外譯乃至中國文 學外譯的一個重要命題。一些文學作品之所以被視 為優秀作品,成為中國文學經典和世界文學經典, 作品的文學性必然是關鍵因素。利奇《指南》一書 為考察以當代小說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性 及其在翻譯中的再現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 參考。上文研究也顯示,餘華《在細雨中呼喊》這 部小說具備利奇總結的全部八種語言變異情況。但 是對小說英譯本的檢視顯示,譯者在面對原文語言 變異時的翻譯處理整體而言重視不夠,譯文美中不足。這應該不是譯者能力的問題。像語音變異、方 言變異等因為語言、文化之間的固有差異,確實不 易妥善處理和完美再現,但其他變異情況還是存在 一定操作空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做到既觀照原文 作者,同時又考慮到目的語讀者。《在細雨中呼喊》 的譯者白亞仁也曾坦言:“一位譯者也必須是一位 敏感和警覺的聆聽者。只有這樣,譯者才不會將原文直接、機械地翻譯出來,而能發掘對象語言的內涵, 充分表達原著的意思,並重新創造原著帶給讀者的 種種感受。”[16]
參考文獻:
- 許宗瑞 . 中國當代文學國外讀者評論研究——基於 Goodreads 網站讀者評論的調查 [J]. 長春大學學報, 2022(11):57-62.
- 查明建,吳夢宇 . 文學性與世界性:中國當代文學海外譯 介的著力點 [J]. 外語研究,2019(3):10-14.
- 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86.
-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姚文放 .“文學性”問題與文學本質再認識——以兩種“文 學性”為例 [J]. 中國社會科學,2006(5):157-166, 208-209.
- 童慶炳 . 談談文學性 [J]. 語文建設,2009(3):55-59.
- 曾祥宏 . 論譯文的文學性再現與譯者主體性的發揮 [D]. 上 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3.
- 孫會軍 . 中國小說翻譯過程中的文學性再現與中國文學形 象重塑 [J]. 外國語文,2018(5):12-15.
- GEOFFREY N. LEECH.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1969.
- 孫會軍,聶士聰 . 變異性表達·文學性·海外中國文學 形象——以閻連科小說英譯為研究案例 [J]. 外國語(上海 外國語大學學報),2022(4):89-98. [11] 餘華 . 在細雨中呼喊 [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 YU HUA. Cries in the Drizzle[M]. trans. by Alian H. Barr.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7.
- PUBLISHERS WEEKLY. Cries in the Drizzle[EB/OL]. (2007- 08-06) [2022-12-25]. https://www.publishersweekly. com/9780307279996.
- 張莉 . 小說裏的新詞與舊詞 [J]. 小說評論,2022(4): 178-182.
[15] 韓子滿 . 試論方言對譯的局限性——以張穀若先生譯《德 伯家的苔絲》為例 [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4): 86-90.
[16] 趙紅娟 . 小說·歷史·文學翻譯——白亞仁教授訪談錄 [J]. 文藝研究,2020(9):102-110.
來源: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網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