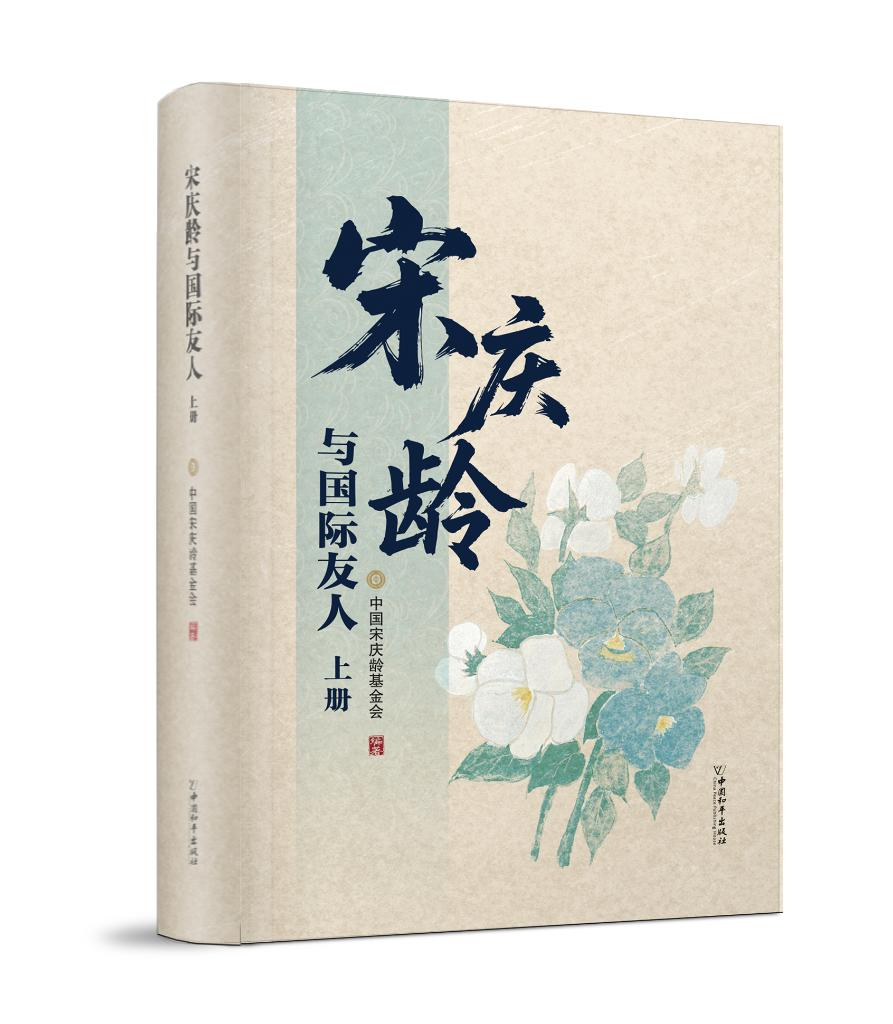本網綜合陳墨報導
1955年,金庸開始連載他的第一部武俠長篇《書劍恩仇錄》,從此開啟了新派武俠時代。“學者線上”特轉載著名金學研究專家陳墨宏論金庸武俠魅力之文章,以饗讀者。

新派武俠是一套文藝的武功
1955年2月8日,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在香港《新晚報》上連載,至今已屆60年,值得紀念。《書劍恩仇錄》與梁羽生此前發表的《龍虎鬥京華》(1954年1月20日至8月1日在《新晚報》連載)及《草莽龍蛇傳》共同標誌著香港武俠小說新時代的開始,梁、金小說被稱為“新派武俠”。
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正處於社會和文化變遷中。其原因,一是隨著香港本土新生世代的成長,其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二是從抗日戰爭開始至新中國建立之初,因避戰亂,大量人口湧入香港,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三是隨著兩岸隔絕,香港成了兩岸政權都十分重視的橋頭堡及競爭地。大量財富湧入香港,也在逐漸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進而改變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
在梁羽生和金庸小說發表之前,香港報紙也連載武俠小說,不過影響有限,且漸趨末路。原因包括:舊武俠大多是粵語方言,發表在粵語報紙上;它們的寫作主題大多是地方武林恩怨、私家情仇;其主人公如黃飛鴻——那時候黃飛鴻遠沒有後來那麼出名–等,也多是廣東好漢;舊小說的寫作方法也相對老套,缺少變化,與新世代的審美娛樂需求逐漸脫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胡鵬導演、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系列粵語電影不斷推出,吸引了大量武俠愛好者。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俠一出現就大受歡迎,進而引領新潮數十年,是因其新思想、新語言、新技法和新趣味,迎合了香港社會的審美娛樂需求。新思想,是指梁羽生和金庸小說都持明確的人民史觀,向人民、反官府,高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旗幟,視野更為開闊,題旨更為深廣。新語言,一是指用國語普通話寫作,讓粵語和非粵語讀者都能接受,讀者面更廣;一是指新派武俠小說都自覺吸收了漢語現代文學的辭彙和語法,讓人耳目一新。新技法,是指新派武俠小說吸收了中西文學的藝術經驗和敘事技巧,如心理描寫、審美抒情等等。新趣味,是指新派武俠繼承了古典章回小說形式,間有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加上大量典章文物、歷史名人和大陸風光,能慰藉香港新老居民北望神州的文化鄉愁。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俠小說。在金庸小說中算不上是最好的,也非金庸迷普遍喜歡的,但它有金庸的創新印記,例如:“百花錯拳”。
“百花錯拳”出現在《書劍恩仇錄》的第3回,小說的主人公、新任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與鐵膽莊莊主周仲英因為誤會,打了起來。開始時,陳家洛使用的是常規武術套路,例如少林拳、八卦遊身掌、太極拳、武當長拳、三十六路大擒拿手、分筋錯骨手、岳家散手等等,陳家洛使用這些功夫都無法戰勝功力深厚的武林前輩周仲英,不得不施展獨門絕技——百花錯拳。書中寫道:
……只見陳家洛擒拿手中夾著鷹爪功,左手查拳,右手綿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時已是太極拳,諸家雜陳,亂七八糟,旁觀者人人眼花繚亂。這時他拳勢手法已全然難以看清,至於是何門何派招數,更是分辨不出了。
……這拳法不但無所不包,其妙處尤在於一個“錯”字,每一招均和各派祖傳正宗手法相似而實非,一出手對方以為定是某招,舉手迎敵之際,才知打來的方位手法完全不同,其精微要旨在於“似是而非,出其不意”八字。
陳家洛使用“百花錯拳”,終於勝了周仲英一招。這套拳法,是第一次寫武俠小說的金庸先生所獨創——他把這套拳法的著作權授予了陳家洛的師父“天池怪俠”袁士霄,袁士霄又教授給陳家洛——其妙處,絕不僅僅是新穎別致,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文化創造的原理:其一,根據小說的敘述,這套武功是袁士霄遍訪武術名家之後,融通百家,別走蹊徑的創造性成果,這符合中國古人所說的“法乎上者,僅得其中;法乎中者,僅得其下;法乎眾者,得乎其上”的寶貴經驗。用現在的話說,袁士霄是學習了多種傳統學科,創造出了自己的邊緣新學科,拓展了武學和武術的邊界。其二,“百花錯拳”的技術操作性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好在它只是訴諸讀者的想像;可以肯定的是,這套拳法的精髓,即似是而非、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肯定符合武打原理,它也是古今戰爭之學的重要原則。“百花錯拳”是一種“理論模型”,是“原理性知識”,而非“操作性知識”。
古人常說文如其人,金庸小說中的武功也如其人:長期浸淫於某種打鬥模式,往往也會影響到創造者或使用者的行為模式乃至認知模式。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認知模式、行為模式影響到打鬥模式的創造和使用。“百花錯拳”的創造者袁士霄、繼承者陳家洛的人生為此提供了例證:袁士霄與師妹關明梅的相戀,但因袁士霄性格和心理古怪,一錯再錯,如百花錯拳一般,傷害了深愛的對象、對象的丈夫陳正德,以及袁士霄本人。
陳家洛的人生,似也被“百花錯拳”所控制。與霍青桐、喀絲麗姐妹的相遇和相愛,也是一再出錯,先是讓霍青桐傷心欲絕,更不可原諒的錯誤是,他竟然答應去勸說香香公主獻身於乾隆,終於讓香香公主不得不自殺身亡!在政治路線和政治謀略上,陳家洛實際上也犯下了一系列的錯。
這套武功,堪稱“文化的武功”或“藝術的武功”,是金庸小說武功設計的典範模式。金庸小說中有很多類似案例。如《書劍恩仇錄》的最後,出現了取自《莊子》寓言故事的“庖丁解牛掌”;《神雕俠侶》中楊過自創,取自文人江淹《別賦》的武功“黯然銷魂掌”,都可以進行具體的學理分析。
關於“百花錯拳”,小說中還有一段關鍵性的介紹:
……須知既是武學高手,見聞必博,所學必精,於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見,不免“百花”易敵,“錯”字難當……
這一段話不難理解,大凡學武的人,總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學習和理解的,也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對付敵方;若是遇到不按既有的套路出手的人,不免就會出現“錯”字難當的局面。武學高手如此,文學高手也這樣,低手就更難免如此。
改造通俗文學的全能冠軍
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中,武俠小說沒有地位,民國武俠小說名家如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宮白羽、王度廬等,向來無人提及。金庸小說是武俠小說,但又確實與眾不同,可謂獨一無二。金庸小說為何有此驚人的魔力?以“百花錯拳”為索引,或可用下麵這些片語來概括:
成人的童話,革新的類型,變化的模式,文藝的武功,個性的俠義,迷離的情感,寓言的傳奇,仿真的虛構,風雅的通俗,反省的鄉愁,現代的傳統。
成人的童話,是數學大師華羅庚先生總結的,我以為,這句話是武俠小說,尤其是對金庸小說魔力的最好的概括。“成人的童話”這個概念,最先是魯迅先生在童話《小約翰》譯本引言中提出的,根據魯迅先生的意思,是指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者的讀物。成人的童話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中國文化而言尤其如此。我們的文化傳統,向來羡慕兒童的“少年老成”,其結果,則往往製造許多“成年的兒童”即心智不成熟的大人。成人的童話,有助於人格心靈的健康成長。
很多人不喜歡武俠小說,這很正常。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沒有讀過武俠小說,尤其沒有讀過金庸,只根據自己對武俠小說的一般印象或想當然來批評,這就不大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了。北大嚴家炎教授在《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中說,金庸小說“是精英文學對通俗文學改造的全能冠軍”,這是對金庸小說的“革新的類型”的最重要的概說。
金庸小說不僅有革新的類型,更有變化的模式。也就是說,金庸小說不僅與傳統的武俠小說不一樣,他本人的小說也在追求變化,每一部作品都與前一部不一樣。《書劍恩仇錄》是一種敘述模式,《碧血劍》就創新了:這部作品的主人公竟然是沒有出場的兩個人物:袁承志的父親袁崇煥和夏青青的父親金蛇郎君。緊接著的《雪山飛狐》有更大的變化,它用羅生門式的講故事的方式,在一日的講述之中呈現百年的歷史,最後,胡斐對苗人鳳的那一刀還不知是否砍下。
金庸小說的革新的類型和變化的模式,是全面的。如果說,武俠小說是由武功、俠義、情感和傳奇幾種重要的因素組合而成,金庸小說對這幾個因素都有重大革新。前面已經說了,金庸小說的武功是“文化的武功”,不必再說。俠義方面,金庸小說是“個性的俠義”,這話有兩重含義,一是金庸小說注重人物的個性刻畫,這是一目了然的:陳家洛是一種性格,袁承志是另一種,胡斐又是一種;“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位主人公郭靖、楊過、張無忌的個性完全不同。其二,金庸小說的價值觀,也是在不斷向現代化方向拓展和深化的。
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的基礎,與其他武俠小說並沒有什麼不同,即行俠仗義、鋤強扶弱、除暴安良;金庸小說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俠義精神在不斷變化拓展,既有基於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俠義,也有個人主義、國際主義、和平主義的俠義。說“國際主義”總有人覺得驚奇,有實事為證:《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段譽、虛竹這三個主人公,都不是尋常的民族主義者,也不能用愛國主義概念來解釋他們的行為和心理,這三個人都是人道主義者,在當時,他們的行為具有寶貴的“國際主義”精神,蕭峰之死,既不是為了宋國、也不是為了遼國,而是為了民族的和平。金庸小說的俠義,並不都是基於集體主義的。從郭靖的“為國為民、犧牲自我”到楊過的“至情至性,實現自我”,就是基於集體主義的俠義與基於個人主義的俠義的鮮明對照,《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顯然也是楊過這一類的,只是個性有所不同。
再說“迷離的情感”。金庸小說的情愛描寫,得到了言情作家三毛的稱讚,這可不是偶然的。金庸小說的情愛描寫,不僅豐富多變,而且充滿了變數,甚至充滿了對人類情感的未知領域的探索:《飛狐外傳》中馬春花一生癡愛的不是丈夫徐錚,也不是商寶震,而是福康安;《天龍八部》中的虛竹和銀川公主相愛,竟然不知道對方的模樣;誰能說得清,《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對嶽靈珊和任盈盈這兩個姑娘的愛,究竟哪個更深;我們也不能判斷;楊過對小龍女的追求,是否能完全抹殺他對郭芙的情不自禁。男歡女愛,既包含身體的欲望,也包含社會的風尚,更包含精神的戀情,其中的每一個維度,都充滿了變數,從而有太多的未知。金庸小說的“迷離的情感”,寫出了人性和人生的複雜度。
“仿真的虛構”包含對歷史的仿真,典型做法是將江湖傳奇和江山歷史融為一體,將虛構的傳奇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集聚一堂。梁羽生先生的小說也是如此,但金庸小說的仿真,不僅包含對歷史的仿真,還包含對社會的仿真和對人性的仿真,進而他還將歷史、社會和人性的仿真,創造成“寓言的傳奇”,這是其他武俠小說所未有的。典型的例證,是《笑傲江湖》,這部小說沒有具體的歷史背景,但我們從中可以讀出三千年中國歷史的寓言真相,政治權力的爭鬥,基於人性,又改變甚至扭曲人性。
金庸小說之所以能夠被全球華人所喜愛,最大原因是華人讀者能夠在金庸小說中獲得鄉愁的慰藉。可以說,金庸小說是寄託文化鄉愁的重要載體或媒介。但金庸小說中的歷史、文化傳統,是經過他批判性思維的產物,自始至終貫穿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到最後一部作品《鹿鼎記》,文化歷史批判精神達到巔峰,對武俠傳統也進行了深刻反思和犀利批判。主人公韋小寶,可與魯迅筆下的阿Q相提並論,可謂歷史文化批判之旅的最佳導遊。所以,金庸小說中的鄉愁是反省的鄉愁,金庸小說構建的歷史文化傳統是經過反思和批判的現代的傳統。
來源:鳳凰網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