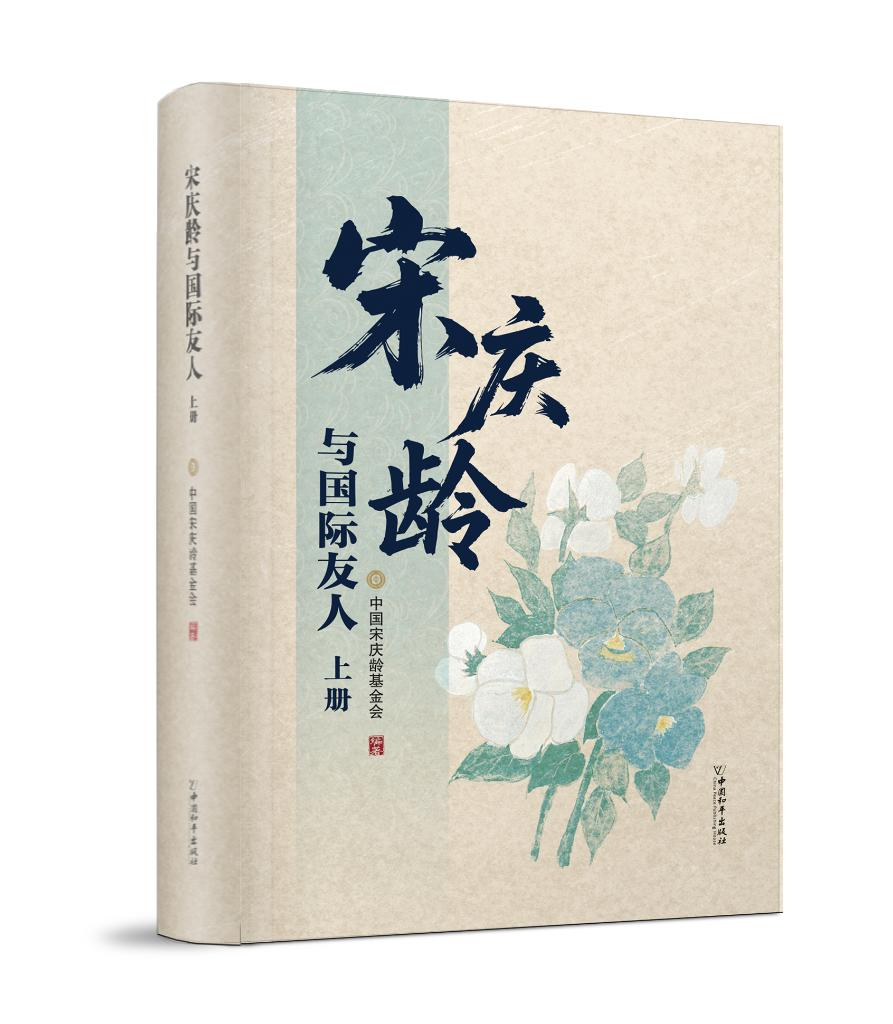本網綜合何玲報導
1927年5月9日,一支由中外科學家聯合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前往包頭,開啟了長達6年的野外科學考察之旅。這是近代以來第一次中外平等合作的科學考察,促成這次合作的關鍵人物是語言學家、詩人劉半農。

“五四青年”
劉半農(1891—1934),江蘇江陰人,原名壽彭,後改名複,初字半儂,後改字半農。1917年,劉半農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等文章,在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破格聘請為北大預科國文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大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軟弱外交,要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劉半農作為北大教授會幹事,“坐守北大指揮部”,積極爭取社會各界聲援。
1920年,劉半農赴歐洲深造,先後就讀於英國倫敦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專攻語言學。劉半農留學期間,曾陪同出訪的蔡元培先生在大英博物館探訪敦煌文書;他還利用業餘時間,將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抄錄下來,輯成一部《敦煌掇瑣》。面對流落西洋的祖國文化瑰寶,劉半農心裏一陣陣地隱隱作痛。
1925年,劉半農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當年回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
維護學術主權
1926年歲末,瑞典著名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到達北京。斯文·赫定此前曾4次赴中國西北探險,以發現樓蘭古城著稱於世。他此行是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資助,準備組織一支大規模的探險隊,為漢莎航空公司開闢一條跨越歐亞的遠距離航線,預先考察地理和氣象情況,並借機進行考古發掘。經斯文·赫定多方活動,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這一計畫。
此時,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中國學術界已經覺醒,民族意識與學術主權意識尤其強烈。斯文·赫定的再次到來,刺激了中國學術界敏感的神經,迅速發起應對行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猛將劉半農充當起主將的角色。
1927年3月5日,在劉半農等人的主持下,北京大學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中央觀象臺等學術機構的代表,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召開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議,討論籌備建立一個永久性機構,以監視外國人擅入中國收集學術材料,不准其隨意挖掘、購買或假名竊取我國文物。會後發表了《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之宣言》,矛頭直指斯文·赫定:
“聞有瑞典人斯文赫定組織大隊,希圖盡攫我國所有特種之學術材料。觀其西文原名為 SvenHedin Central AsiaExpelitian(注:斯文赫定中亞探險隊)已令人不能忍受。夫 E x p el i ti a n 一字,含有搜求、遠征等義,對於巴比倫、迦太基等現代不存之國家,或可一用,獨立國家斷未有能靦顏忍受者。試問如有我國學者對於瑞典組織相類之團體,瑞典國家是否能不認為侮蔑。同人等痛國權之喪失,懼特種學術材料之攘奪將盡,我國學術之前途,將蒙無可補救之損失,故聯合宣言,對於斯文赫定此種國際上學術上之不道德行為,極端反對。”
中國學者的強烈反對,令斯文·赫定始料不及,轉而尋求與中國學術機構合作。
3月9日,斯文·赫定致函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表示願意吸納幾名中國學者參加考察團。次日,斯文·赫定又偕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顧問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前往北京大學與中國學者見面。斯文·赫定顯得很傲慢,只寒暄幾句,便匆匆告辭,留下安特生與中國學者會談。初次見面,斯文·赫定注意到了說一口流利法語的劉半農。
3月14日,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議致函斯文·赫定,明確表示在中國境內進行的科學考察必須由中國人主辦,同時願意與他“作友誼的晤談”。沈兼士也復函斯文·赫定,推薦劉半農與他商談。當時中國學者考慮到自身經濟實力不足,又缺乏大規模野外考察的經驗,有意在堅持學術主權的前提下,與斯文·赫定進行一次務實的合作。
3月19日,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議改組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確定為永久性機構。為了維護學術主權,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制定了《關於在我國境內進行學術考察的六項原則》,明確提出:中國境內所有之學術材料由中國學術團體調查或採集,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調查或採集,但於必要時,得容納外國專門人才或學術團體參加,以資臂助;採集所得之材料,應在中國境內妥為保存,非經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特別審查及允許,絕對不得運出國外。
三次會談
3月2 0日,劉半農等5位中國學者前往斯文·赫定下榻的六國飯店,與他進行第一次會談。劉半農詢問得很仔細,包括斯文·赫定此行目的是否涉及軍事內容,考察團的成員是學者還是軍人,為何考察地磁學,地圖如何畫法,考古發掘物如何運送,等等,要求斯文·赫定作出書面答復。斯文·赫定覺得“這次會面仿佛是一次公正的法庭調查”。“整個庭審期間,對方表現的倒很客氣和和藹,同時,他們語言邏輯上的鋒利及其透人的深度又令人震驚”。
3月22日,斯文·赫定不顧雙方正在商談,執意按照自己的預定計畫,派遣11名歐洲團員作為先遣隊,從北京向包頭進發。劉半農聞訊後,立即致函斯文·赫定,警告說如果他自己再離開北京,就將發動整個中國新聞界一起反對他。同時,中國學術團體學會還致電綏遠都統,請求監視外國人的考察活動,並將電文公諸報端。北洋政府外交部懾於學術界的壓力,也告知斯文·赫定,假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極力反對,政府將會考慮撤回考察團的旅行許可證。
3月25日,劉半農等人再次前往斯文·赫定的住所,與他進行第二次會談。劉半農提出這次考察活動必須由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主辦,中國學術團體學會將成立專門的理事會,管理考察團的一切事務,考察所得物品應全部交與理事會保管,中方將派遣10名學者和5名學生參加考察團。斯文·赫定一開始充滿了抵觸情緒,聲稱這是強加給他的“凡爾賽和約”。劉半農與斯文·赫定進行了一番學術性長談,使他的態度逐漸緩和下來。斯文·赫定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告訴劉,我很同情他們的民族主義態度,因為在我自己的國家裏,我與他們一樣,也是個民族主義分子。我認為,他們希望將所有的考古與藝術發掘品留在中國是正確的,自從鴉片戰爭之日起,歐洲人在中國人民身上已經犯了一系列錯誤。”
4月2日,劉半農等中國學者與斯文·赫定在北京大學進行第三次會談,逐條討論雙方合作的意見。斯文·赫定提出:他獨自承擔這支龐大考查團的費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應該對他所付出的代價略作補償,希望能得到考古發掘物的“重複物”。中國學者再次拒絕了斯文·赫定的要求,表示“重複物”這一概念實際上很難定義,比如說發掘出5個相似的罐子,即使它們完全相同,但也很難將它們分得合理。
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交鋒,斯文·赫定終於接受了中國學者的意見。4月26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會長、古物陳列所所長周肇祥與斯文·赫定分別代表中外雙方,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簽訂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主要內容處處體現了中國的學術主權:“第一條、本協會為考查西北科學事務,容納斯文赫定博士之協助,特組西北科學考查團。第二條、本協會特組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依據本合作辦法,監察並指揮該團進行一切事務。……第十條、凡直接或間接對於中國國防國權上有關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如有違反者,應責成中國團長隨時制止。第十一條、旅行時所繪地圖,除工作所用區域外,其比例不得大於三十萬分之一。第十二條、考查時應守之規定如下:不得有藉口,致毀損關於歷史、美術之建築物,不得以私人名義購買古物等。……第十九條、本訂定辦法,附有英文譯本一份,應以中文為准。”
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第一個中外平等的協議終於誕生了。近代以來,一部西北探險史就是中國學術文化的傷心史,劉半農面對這份協議,情不自禁地戲稱這是“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平等合作
在隨後的6年時間裏,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三十多位中外團員平等合作,足跡遍佈內蒙古、新疆、寧夏、甘肅、青海、西藏等地。中國學者利用這次合作,走出了書齋,取得了開拓性的成果。丁道衡發現了白雲鄂博大鐵礦;袁複禮發現了天山恐龍化石;黃文弼和瑞典的貝格曼發現了“居延漢簡”;陳宗器和瑞典的霍涅爾進入羅布荒原,完成了繞羅布泊一周的實地考察,繪製了羅布泊地區的第一幅實測地圖;李憲之和劉衍淮在德國氣象學家郝德的指導下,在柴達木盆地建立氣象站,駐守觀測寒潮,後被郝德推薦到德國柏林大學留學,雙雙獲得博士學位。
中國學者的成就,改變了斯文·赫定最初的傲慢與偏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與中國朋友的合作是完美的,在一起情同手足。能有這種殊榮去與中國的一些最傑出的學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著友情與感謝,將終身銘記他們中的每一個人!”
劉半農沒有赴西北參加野外考察,他在北京大學主持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的日常工作,被斯文·赫定稱為“理事會中的靈魂和真正的核心”。
來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