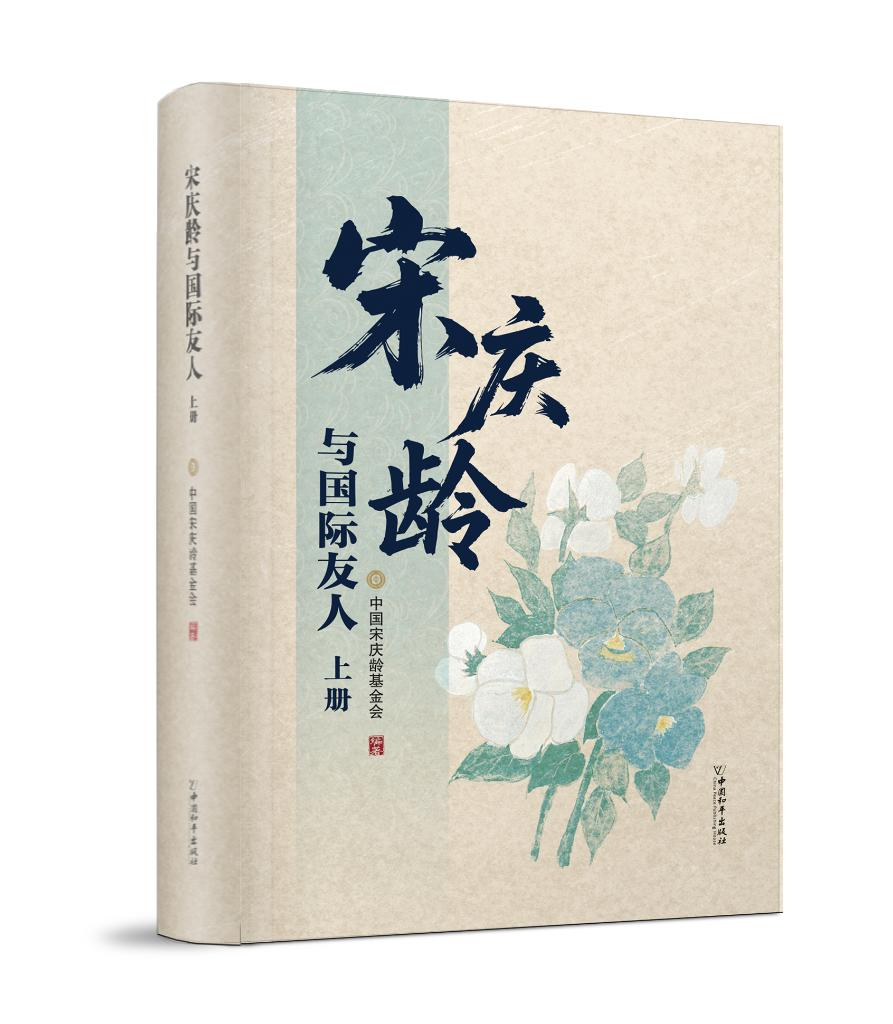全球視野下的精神人文主義
[美]杜維明
提 要 基於儒家傳統的精神人文主義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實現人類持續繁榮與昌盛的管道,或將有助於各種思想、宗教、文化傳統發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識,以解決整個世界人類所碰到的困境,而這也有助於世界各國關係的改善。 而中國傳統思想中以孟子為代表的心性之學,以“仁”為核心的“性善論”等觀念,實則是強調發揮個人的主體性,如此能夠推動我們與他人、與社會、與世界的和諧共處。 這一精神人文主義在實踐中應把握四種關係,分別是自我本身的內在關係、將心比心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個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性與天道的相輔相成。
關鍵字 精神人文主義 儒家 孟子 全球 現代
中圖分類號: 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5 - 3247(2023)03 -0050 -07
一 問題的提出
我提出的是紮根於儒家傳統的“精神人文主義”(Spirtual Hunmanism)。 那麼,精神人 文主義是否能在當前中國乃至全球湧現? 儒家傳統作為一個源遠流長、且有全球意義的 地方性知識,對於當下人類遭遇的困境,究竟有無可應對的方案? 我研究儒家文化始於孟 子心性之學,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學發展出精神人文主義,使之能與目前人類棘手的倫理學 危難相關聯? 這是個集體課題。 在此,想與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並不很樂觀的思考並以 此拋磚引玉。
我認為,精神人文主義是一個正在湧現的全球性論域。 表面上看,這一思想並不涉及 多極化世界下中國崛起並正在成為重要一極的問題,就更寬廣的視野而言,這個問題其實 關聯著人類如何能夠找到一條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何通過文明對話達成文化諒解並 建立對話的文明,如何與地球形成一種可持續的關係等方面。 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有賴於 一種新的思想的出現。 在我看來,這就是基於儒家傳統的精神人文主義。
二 精神人文主義與啟蒙反思
關於精神人文主義這個論域,它首先是產生於對啟蒙問題的反思。 在人類過去的幾 百年中,啟蒙運動及其構想的人類整體計畫,在歷史上起著極大的作用。 資本主義誕生於 它,而社會主義則是對它的一種突破。 在過去幾百年的歷史實踐中,財富和權力成為人們 最關注的對象,而啟蒙之前人們所珍重的東西則不再被重視。 由此,世俗性的人文主義事 實上成為了主導世界的意識形態。 所以,我們亟需在啟蒙運動之後,對它帶來的諸多不良 後果進行反思。 這些不良後果包括帶有侵略性的人文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佔有 性的個人主義。
針對世俗性的人文主義而提出的精神性的人文主義,則宣導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對 天敬畏、對地球尊重和愛護,進而建立一種互相信賴的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並以天 下太平為文明對話的目的。 所以它特別強調和解與和諧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認為,“和” 的對立面是“同”,而“和”的前提條件是“異”,這種認識和近五十多年來西方的女性主 義、環保主義、多元文化論、宗教多元論等所提倡的觀念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這樣一種人文主義的出現,是我們設想一個真正意義上永久和平的世界能否出現的 先決條件。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具有各種文化,中國的、印度的、希伯來的、希臘的等, 它們都提出了與現代的哲學、宗教、文化有密切關係的理念。 而面對現在這樣一個全球生 態環保失衡、世界社會秩序重組的時代,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明都需要經過一個重要的轉 型,以促成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精神的出現。 每個人都可以是信奉不同哲學理念、信仰不同 宗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但是每個人其實都面對著當前世界的共同現狀,也就是我 們整體人類所遇到的存活的困境。 這就要求我們除了有一種特殊性的背景外,還要有一 種站在全人類高度的思考。
所以,真正能夠指引我們在21世紀生存並持續繁榮的思想,應該可以拓展我們從啟 蒙運動發展以後被狹隘化的心態,而獲得一種更加深沉厚重的道德積蓄。 其中最低的要 求是,我們要能超越我們這個時代各種狹隘的特殊主義,世俗的人文主義就是其中一種, 而在世界各地正在興起的國族主義、民粹主義更是其中的典型。
近代以來,文化中國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整體遷變,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與 文化的文明體,通過努力去重新發現、重新修復、重新建構自己,而更新了自己。 也就是 說,中國文化不僅不是過去,不僅不是歷史,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大傳統。 我們大家其實 也都正在參與在這樣的一個工作中,我們與歷史正在對話中相遇,這是令人鼓舞、令人興 奮的。 而這樣一種更新的過程,使得中國人發現了能與世界分享的一種豐富的意義資源、 寶藏,它在中國還活生生地存在著。
總之,現代中國除了給世界帶來政治、經濟方面的新道路外,還應當在文化角度對世 界有所貢獻。 而這個貢獻所帶來的成果應當並不是中國強迫全世界的人接受的,而是它 更具有包容性、涵蓋性,它是一條真正寬廣的路,能夠讓全世界的人都行走在上面。
我所提倡的基於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義,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實現人類持續繁榮 與昌盛的管道,它或將有助於各種思想、宗教、文化傳統發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識,以解決整 個世界人類所碰到的困境,而這也將有助於世界各國關係的改善。 因為這種人文主義,要 求各國家、各民族之間的融通、互信、瞭解,這是對他者的一種尊重,也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三 精神人文主義與儒家核心價值
我們作為中國人,要想探索這樣一種思想,能脫離傳統麼?當然不能。一種在中國興 起的人文主義,天然地和中國的儒家、道家有關系,否則它將缺乏深沉、深厚的思想根基。 而且,只有具有這種深沉、深厚的根基,它才能帶給人們以當今這個時代所最缺乏的敬畏感。 我們常說,年輕一代迫切需要有一種敬畏感的培養,即對天地自然的敬畏、對超越財 富與權力的整體人類世界的敬畏,但如果這種敬畏感沒有紮根於本民族文化傳統中,則它 是很難產生真正作用的。
具體到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學的傳統,在不同時代中具有不同的特殊價值,都是一種 對人的重新認識。 強調孟子是一個“性善論”者,其實他說的是做人的道理。 人在整個人 類生物轉化中的出現存在何種意義與何種價值? 我們如何去認識這種意義和價值?個人是否可以通過自身努力發展這種資源,還是必須受外在影響才能發揮自己的力量? 同時,作為一個人,我是否能通過自覺與反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之所以能夠發揮更大價值的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社會環境還是其他原因?
孟子“性善”的觀念是指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內心的惻隱之情,即內心對外部環境 的健康反映,發揮自己做人的基本價值。 這讓我想起西元前800—前 200年的軸心時代,印度文明、希伯來文明、猶太文明與中國文明四大文明同時出現。 當時只有中國文明未曾 出現在被學術界中稱作“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終極的價值關懷必須超越到現實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個理想世界裏。
孔子選擇的人生意義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 由於這種外在超越的“缺失”,因此許 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過於關注現實,沒有更高的意識與價值,沒有到達“超越”這一層 面。 但孟子認為,一個人有很多向度,應當同時開展。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向度就是個人的 主體性,它和人的四端密切相關。 因此,儒家傳統是面對當時的存在對人類進行的反思, 與亙古時代相比,是一個質的飛躍,那就是人類開始探索抽象且永恆的大問題。
“四端”是儒家稱人應有的四種德行,包括仁、義、禮、智。 其中,仁的這一端發自人的惻隱之情,包含著同情的意思,這種惻隱之情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能夠充分發展人性最 重要的資源。 情的感受雖是個人且每人有所不同,但孟子認為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夠 將情推己及人,就逐漸可以將個人、家庭、鄰里、社會甚至國家、天下都聯繫起來,成為一種 向外推的精神世界。這種推己及人的情,發展到陸象山、王陽明時期,他們提出必須要優 先樹立我們作為人的大體,即道德理想的最高價值。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人就要做一個能 夠體現人性光輝的人,做一個像樣的人。 陸象山曾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 堂地做個人”。① 做人,就應做一個對得起自己的人;立志是立自己的大志,可以推到家 庭、他人即為大志。 這也是孟子所說的“先立乎其大”。
對於“四端”之一的“仁”,目前許多中國學者的研究已做出較大貢獻。 在馬王堆出土 的資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為仁,這與一般意義上說的“仁”字有所不同,具 有非常深刻的哲學意義。 人的價值既是內在的、自我的,也是涵攝在關係網絡中的。
通過對孟子的瞭解,我認為仁愛的“仁”是指個人的主體性,這類似於康德說的“自由 意志”。 每個人都要有自由意志,沒有理性就不會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道德人。 而儒家 仁愛的仁裏包含的情,是為他人而生,生髮到一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主體與其他所有人進 行對話,而這種相互對話所形成的社群以仁愛為主。 仁愛不僅僅是愛人,而且還要愛物、 愛己,三者不能分離。 這就是孟子說的“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 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
由於儒家傳統中存在一種強烈的自由度,即我要發揮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選擇。 因此,“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論語·子罕》)就是孔子主動自覺的選擇。 這一 觀念發展到陸象山就是“心即理”,到王陽明是“致良知”,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 每個人內在都有仁心,所以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是科學無法反證的。 也就是 說,我們的心對外在世界有著無限反映的可能,它開放、多元、包容,從最遙遠的星系到眼 前的草木瓦石,對我們的心量來說,都可以到達。
那麼,如何到達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精神世界呢? 這是一個人成為獨立自覺的人必 須要走的路。 首先,仁一定是在人的成長、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豐富的。 王陽明說,每一 天都相當於春夏秋冬的過度,都是新的一天,都有一種新的意念, 這就是生生不息。 其 次,仁者,覺也。 仁也是一種覺悟,他的力量與所有人都能夠成為一體,所以他有公心。 第三,仁能通達,一定要往外通。人的主體性的本體意義在於,能與天打通,因為以天地為 性,因此心靈從天而來。 所以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 盡心上》)。
第四,仁的包容性。 仁可以與其他德性相通,例如禮、義、勇、智、孝等所有價值都與仁 以及佛家說的慈悲有著內在的密切關係。 這是個非常簡單的思路,但要證明它、發展它, 使之成為制度、成為行為習慣,這是人類發展過程中了不起的大事。 仁在中國的不同時代 乃至不同文化中都能顯現這種價值的光輝。
從仁的價值往前看,如何面對現在人類遭遇的存活困境,嚴格來說,就是人還能在地 球上生存多久的問題。 自然世界有其內在的價值而非僅僅具有外在價值。 從科學發展 中,我們瞭解到,人曾是地球演化過程中的累贅,而現在卻成為演化過程中的積極因素,影 響了包括化學、生物各過程在內的整個演化過程。 由於人的投入不斷繁衍,促使演化過程 向後拓寬,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在地球能否生存,能否發展,僅是人從私利角度在考慮問 題,按照中國“天生人成”的觀念,人就應該思考如何與地球相輔相成地存在。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仁”與“禮”的關係是中國哲學界很重要的一個話域, 假設突 出“仁”,那麼,西方哲學界特別重視的“禮”就會受到限制。 “禮”就是發展制度,進而推 進制度形成的一種文明意識,具有許多豐富的內涵。 只強調“仁”而忽略“禮”必然走不 遠。 反之亦然。
非洲有句話,“我的存在是因為你的存在”。 這和儒家思想之“仁與禮的創造性的張 力”其實是一致的。 做哲學研究就是要有陽明說的“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 方有著落”,①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根源意識,就會成為抽象的包容主義。 在儒家思想上 “接著講”的“精神人文主義”就是以仁為“頭腦”,但又開放包容,涵攝天地群己,注重交 流對話。
四 精神人文主義與文明對話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多元現代化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有西方所代表的現代化和全球 化,也有中國所代表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印度所代表的現代化和全球化乃至非洲所代表的現 代化和全球化。 因此,我們需要向其他各個文明進行學習、瞭解,其目的並不是說要放棄我 們的根源性、地方性、特殊性,而是要把我們的根源性、特殊性擴大,擴大到可以包容整體人 類。 因為只有能夠包容,才可能逐漸成為人類都認同的一種真正意義下的人文精神。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對於價值的理解和西方並不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看 來,正義的價值和自由一樣重要;同情比理性更必要;人的責任,特別是一個人對家庭、社 會、人類的責任,比權利更重要;禮治比法治更基礎;社會的和諧比個體的發展更優先。
但是,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傳統中國的這些價值認可仍是有其現代意義的,另外一方面也要瞭解,自由、理性、權利、法治等也是核心價值。 所以,我們需要建構 的是一種可以容納盡可能多層重要價值的人文主義,我們應注重關係、注重和諧、注重人對社會的責任,而同時也注重自由、注重法治、注重權利。 也就是說,基於儒家思想的精神 人文主義,要走的是一條能夠充分容納當前有關人的重要價值的道路。立基於此,我們既可以與其他文明進行真正的對話,也可以批評各類負面的、特殊性的價值觀念。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跳出一種狹隘的、武斷的、過分簡化的方式,來建設一種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 義。 印度思想家南迪②曾說,如果印度的民族主義不包括甘地和泰戈爾,那絕非真正的愛 國主義。 同理,中國的愛國主義必須包括民族的核心價值。
我本人的學習過程是一種真正的文化間的交流,這種交流其實始於東海大學大四時期。 那時,一批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哈佛、芝加哥等精英高校的教授來東海大學, 我們跟隨其中一位學習英文,越來越多的學術交流隨之不斷展開。 赴美留留學,我感到自己 與五四時代前往美國留學的中國學者不同。 我並非完全拜師,自認為還帶有一些使命——同他們交流儒家學說。 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國的資訊相當開放,很多學者願意認真 瞭解我的觀點。 這使得我能在文明對話的基礎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發掘儒家心 性之學。
在我踐履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我發現儒家傳統中的很多內容,不僅是關於地球的,而 且是關於整個宇宙的。 如孟子所講的“天”、宋明理學所講的“天理”,它們乃是從宇宙的 角度來關懷人類,而這個關懷可以和世界各個文明發展出來的重要的精神主義相互配合, 而構成一種更加符合人類未來的精神人文主義。 也就是說,每個人在自己可以扮演的諸 多獨特的角色之外,還有一個無法選擇的根本——每個人都是人。 而我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義,就是試圖從這個角度立論的。
五 精神人文主義的實踐經驗
第一個實踐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成為文明對話的共識。
2001年是“世界和平年”和“文明對話年”,聯合國邀請18位世界各界思想家討論用 何種價值重建文明的對話。 當時德國思想家孔漢思提出用基督教的金科玉 律,即“己所欲,施於人”作為人類在文明對話中的最基本共識。 我在原則上同意他的意 見的同時提出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 《論語·衛靈公》)更適合作為文明對話的基礎。
“己所欲,施於人”是自己以為最好的理念應該跟他者分享,也希望他者可以接受,這 是一種非常好的利他主義,但是我如果過分的執著,我會認為他者理應接受,而如果他者 不接受,我不會立即認為自身有問題,而會認為他者對我瞭解不夠,從而會用一種比較更 有說服力的方式令他者接受,這樣就會引發各種各樣的衝突。 比如在兩個非常不同的價 值領域進行對話時,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是你認為不好的東西,不要強加於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雖然是一個消極語言,但在這個消極語言背後還有一種積極的元素,這就是瞭解 他人、尊重他人、承認他人、互相學習、互相參照的精神,由此出發,文化溝通、文明對話就 成為真實可能的。 應當說,這種價值雖然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儒家話語提出,但 它絕不是儒家獨享的價值,也不是中國人獨享的價值,而是達到真正互惠溝通的道理,是 所有當前人類碰到現在的世界困境時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基督教的金科玉律與儒家恕道文化中有相通之處,這中間引申出的就是仁道,自己發 展的同時也要幫助他人發展。 這次討論的結果是大家達成共識:我們應當開發各種文明 資源,發展世界文明對話,促使世界逐漸形成一個對話的環境。 第二個實踐是2018 年8 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哲學大會。 我提議的“學做人” 被西方哲學界接受為官方的大會主題,“L earning to Be Hunman” 被翻成多國語言,中文表達是“學以成人”。 會議委員會經過考慮認為,在“學以成人”的 主題之下,自我、社群、自然(地)和精神性(天)四個向度缺一不可。 由此看,我們應該把 握四種關係。
第一種是自我本身的內在關係,就是身、心、靈、神的統一。 個人的身體、心靈、靈魂和自己最高的理想進行融合,這種融合形成的作用力來自於內部的反思。 除反思外還需有 一個內在的意識,即良知。
第二種是將心比心的個人與他者的關係。 他人可以是個人或社會,正是我們自我了 解的另一種情況。 個人與社會如何進行健康互動? 這才是最早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理念。 修身是基本,齊家和治國是同步關係。 比如當下,我們應當通過互聯網發揮正能量,這源於每一個人的力量,但同時也對社會有貢獻。
第三種是與自然的關係。 人類與社會、人類與自然需要一種持久的和諧,這樣不僅對 人有價值,對天地也有價值。
第四種是人性與天道能夠相輔相成。 錢穆先生認為中華民族對世界的貢獻就是“天 人合一”,我延伸為“精神人文主義”。 錢穆先生在96歲高齡時口授完成其最後一篇論 文,闡述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人性與天道合一,即天人合 一。 這樣就意味著人不僅對這個世界的持續發展負有責任,還應對存活環境的大自然負 有責任。 我認為,這四個向度的理解要兼顧各種視角。 第一是全球視角,我們不能自傲地認為 這只是中國的傳統與價值,而應將其推廣至世界。 第二是從己出發。 孔子提出“學做人” 就是“為己之學”,旨在發揮自己的潛能並推己及人。 如孔子對顏回所說,“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依靠自己而非他人達到仁。 “己”就是我說的主體性,這在儒 家傳統裏非常關鍵,不可忽略。 心體現仁,不僅可知他人,也可以知天。 這個觀念建立在 個人的主體性之上, 這勢必要破除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破除家庭的局限,否則個人就沒 有滲透力,參悟到社會、國家、天下甚至是宇宙。 “中國就是天下,中原就是天下”的觀念 與孔子、孟子的思想大相徑庭。 天下不僅是普天之下,它還應該包括宇宙論,同時也包含 本體論所提出的相關問題。 所以,我在1980年代提出過“存有的連續性”話題。
六 餘論
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的四個向度(Four Dimensions),是我同基督教、佛教、伊斯蘭 教以及許多其他宗教對話後,逐漸摸索到的人文價值,而這一人文價值是否具有持續性仍 需要經受考驗。
例如,一個基督徒能否認同這一說法,並且不放棄自己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信仰? 一個佛教徒、馬克思主義者是否在面對人類當下困難時,都能不脫離這四個向度? 我 認為是。 因此,現在出現許多非常有趣的現象,有“波士頓的儒家”,有伊斯蘭教徒自稱 “回儒”或“儒回”。 也就是說,各個不同的宗教領域都出現了一種新的人文精神。 又如, 基督徒原本不太注重生態環保,因為這是屬於上帝治理之事,但具有精神人文主義的人就 應該重視;以前的佛教徒追求四大皆空和究竟涅槃,但現在要在完成個人自己的修行的同 時,自覺地將人間作為一個道場,這或許就是“人間佛教”的由來。
以上是目前我對精神人文主義的一個框架性的認識,供各位參考。
本文根據杜維明先生在2016年華東師範大學“桑德爾與中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及2017年北京師範大學“首屆京師中哲名家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整理人王建寶,校對陳茂澤、黃琦。
作者簡介:杜維明(1940-),男,祖籍廣東南海,生於雲南昆明,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 語言學博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國際哲學學院院士 兼副主席,臺灣“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儒學等。
-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六》,《黃宗羲全集》第 8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 2117頁。
- ① ② 黎業明:《王陽明傳習錄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01頁。 阿希什南迪(Ashish Nandy,1937-),印度政治心理學家、社會理論家和批評家,曾擔任發展中 社會研究中心(CSDS)高級研究員和主任。 作為一名臨床心理學家,南迪對歐洲殖民主義、現代性、世俗 主義、印度教、科學、技術、核主義、世界主義和烏托邦主義進行了理論批判。
來源: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









 您當前的位置 :
您當前的位置 :